近日,《洛桑的家事》亮相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双周影院”第三场学术交流放映活动。这部已斩获2022全亚洲独立电影节(AAIFF)故事片单元“最佳影片奖”的电影,讲述了生活在西藏乡村的三家人的命运因为一场车祸悲剧交织在一起的故事:洛桑5岁的孙女央金被酒后无证驾驶拖拉机的豆拉伽撞瘫,洛桑想起诉豆拉伽并让他坐牢。肇事者豆拉伽是个跛脚的残疾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本就困难,为了赔偿洛桑一家已经掏空了家底。如果豆拉伽去坐牢了,他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妹妹卓玛欲照顾哥哥豆拉伽的孩子,又被丈夫所阻止,两人的婚姻也岌岌可危……看似简单的乡村冲突,在西藏独特的人文背景和纪实性的叙述下,于宽容与和解中透出人性和生命的闪光点,呈现出更大的戏剧张力。这个有关爱与理解的故事,体现了法律与人情、信仰与生活的交织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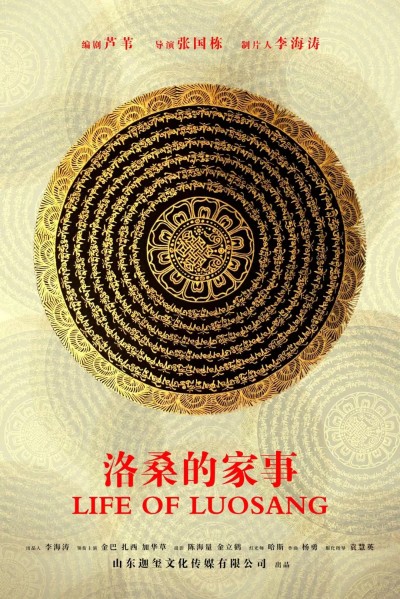
内视化、平视化的叙事视角
囿于地域和文化心理的差别,以往国内非藏族导演在讲述藏族题材故事时,可能无意识地将书写的重点放在藏族聚居区空间文化,某种意义上遮蔽了真实的藏族聚居区空间。这表现为例如用大量的空镜头描述藏族聚居区独特的地理空间,以帐篷指代藏族群众的生活空间,少有现代元素出现。偶尔有导演尝试用一种兼容了藏族本身的视角来讲述藏族题材故事,却由于怀有“膜拜、朝圣的心态和情怀”,而不自觉将西藏神秘化。尽管本片导演张国栋和编剧芦苇都不是藏族,但他们在作品中却没有像以往国产藏族题材电影那样,呈现一个传奇式、奇观化的西藏,而是以近乎纪实的拍摄手法,白描了一种当代西藏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在社会层面保留了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没有磨掉藏族独特的元素。
影片在藏语女声的吟唱中开始,雪域高原随着航拍镜头徐徐展开。除了藏语方言对话、藏族谚语和歌谣等西藏元素外,雪山、高原草地、林场小道、喇嘛寺院、藏族村庄、牧场帐篷构成了影片中独特的藏族聚居区地理空间;牦牛、野狼、祝酒歌、藏戏、经幡、风马旗、祈福仪式等藏族聚居区独有的意象和符号也在影片中有所体现。但是,影片没有减弱对藏族人民现代化生活的呈现。影片中出现的人物不仅穿传统藏族服饰,也穿现代服饰,智能手机、汽车、广播电视塔时有出现,主人公对话时出现的广播背景音,酥油茶与可乐、啤酒同摆一桌,种种细节都体现出影片的纪实感和内视化、平视化。
正如影片片名所暗示的,《洛桑的家事》的叙事视角是内视化的,是一个普通藏族群众的“家事”。影片的故事线是清晰且完整的,因果逻辑也是合乎常理的,站在洛桑的角度,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毫无缘由的和解。一开始,洛桑想要肇事者豆拉伽坐牢的心意是坚定的,豆拉伽酗酒、自暴自弃,并且一直没有去他们家里真诚道歉。转变是从豆拉伽的儿子逃学去挖虫草开始的。豆拉伽得知了儿子逃学的真相——挖虫草帮助父亲早日凑齐对央金的补偿金后,掩面哭泣、幡然醒悟,振作起来,真诚悔过。此后,无论洛桑、诺日(央金的父亲)对豆拉伽态度多恶劣,豆拉伽都坚持去给诺日一家补偿、赔罪。后来,诺日的妻子在遥远的冬牧场不慎早产,豆拉伽冒着风雪去请自己的妹妹卓玛(村中唯一的乡村医生)来接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洛桑一家感受到了豆拉伽的另一面。
该不该和解?洛桑面对的两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两难。这个故事中没有真正的恶人,无论是洛桑、诺日、卓玛,还是肇事者豆拉伽,都是立体的、非脸谱化的。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藏族元素强化着影片的“内视化”和“在地性”,观影者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某个中国农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
基层社会的多主体参与
洛桑一家与豆拉伽的和解体现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逻辑。可以说,基层社会能够和谐运转、矛盾纠纷得以化解,离不开基层社会多主体参与调和。首先出场劝和的是村主任。村主任三番五次来到洛桑的家中,劝解洛桑放弃上诉,因为“豆拉伽是个苦命的人”,而且如果他去坐牢了,他的两个孩子可能要被送往福利院生活。正是在村主任的组织下,洛桑一家与豆拉伽召开了一场调解会议,尽管这场会议没有达到村主任预期的效果,但是调解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而另一方面,影片中,诺日的弟弟是一名喇嘛,他受住持的点拨,专程回家劝解父亲放弃上诉,进而“种善因、结善果”。
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洛桑认识到,即使把豆拉伽送进监狱,央金的腿也好不了,反而会让豆拉伽的家庭支离破碎,同时鉴于豆拉伽已经真心悔过,于是他放弃上诉,选择和解,此为“种善因”。影片中,诺日的妻子和豆拉伽的妹妹卓玛相继早产,都生下了健康的孩子,并约定让两个新生命长大后一起照顾央金,这预示着新的开始;影片的结尾,央金尝试自己依靠栏杆站起来,虽然导演没有告诉观众最后央金是否真的站了起来,但通过升格等表现方式,将故事的结尾指向“圆满”,这些都象征着“结善果”。
某种程度上说,三个家庭矛盾的解决,也是藏族聚居区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的结果。法治的力量给了豆拉伽罪错感,德治的力量激发了豆拉伽的愧疚感,最终他承担了自己在法律上应该承担的后果,也用实际行动获得了洛桑一家的原谅,得到了精神上的救赎。
藏族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
影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便是豆拉伽的妹妹卓玛。卓玛是一名乡村医生,卫校毕业,是觉醒的现代藏族知识女性的化身。知识使她在乡村生活中发挥了主体性:她有着专业的知识和精湛的业务能力,小到感冒发烧、大到接生,她是当地村民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她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与主见,宁愿冒大风雪也要赶到牧民的家中为牧民治病,宁愿与丈夫离婚也要照顾豆拉伽的两个孩子;她也继承了传统藏族女性的美德,勤劳、能干、自信。与她形成对比的是诺日的妻子。诺日的妻子是传统的藏族女性形象,她善良、悲悯、勤劳,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孝敬长辈,即使怀孕8个月,也要挺着孕肚骑着马去冬牧场协助丈夫放牧。
性别角色塑造就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本片中卓玛的形象塑造也反映了目前藏族知识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性别角色不仅是生理特质赋予的,更多的是由特定文化形塑的。以前大多的藏族题材电影要么遮蔽了女性角色,要么强调藏族女性角色对家庭的贡献,她们作为家庭生产单元发挥作用——不管是农业还是牧业,藏族女性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力角色。即使是“出走的女性”,也是“为爱出走”,她们的反抗也是“依附性”的。长期以来“女性=家庭”的社会思想,束缚了藏族传统女性的发展,形成了藏族传统女性任劳任怨、不反抗、妥协、以男性为尊的社会心理。而卓玛体现出来的是新时代藏族女性发挥主体性的一面,她所做的选择完全基于她的知识,是她的自主选择。乡村医生这个社会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她的社会地位,她能够作为洛桑一家和豆拉伽破冰、和解的润滑剂。
然而,卓玛的自我觉醒是不完全的,随着孩子的降生,卓玛与丈夫实现了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印证了这部电影的纪实性,身处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藏族女性,或许正面对这一切:旧的性别秩序没有完全打破,新的性别秩序尚未完全建立。
(作者:樊雪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慧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