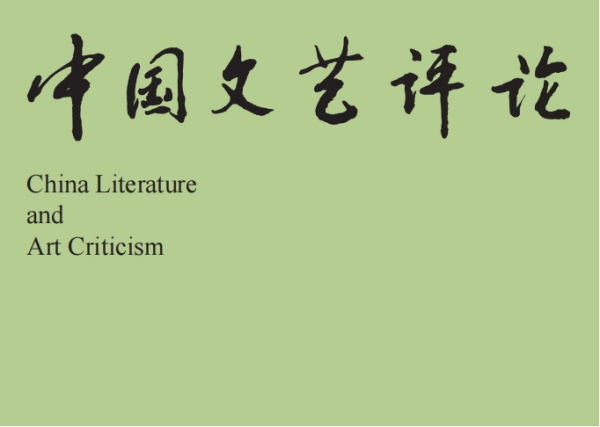
【内容摘要】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关 键 词】 《我的阿勒泰》 跨媒介改编 共同体叙事 如画美
在创意先行的新文旅时代,文学IP成为文化产业转化的重要路径之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借助影视改编,尝试摆脱“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窘境,重新激活文学参与公共生活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为文旅深度融合及地域形象建构提供优质文艺资源。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白鹿原》《人世间》《回响》《繁花》都曾被成功改编成电视剧,文学经典经过跨媒介文本转化,借助视听媒介的传播优势,在文学想象、历史记忆与现实关切之间架起桥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原著的意义空间。此外,网络文学改编剧《甄嬛传》《琅琊榜》《步步惊心》《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庆余年》等风靡荧屏,催生出现象级的大众文化景观。2024年,根据新疆作家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改编的八集同名电视剧,由央视一套黄金档及爱奇艺微尘剧场同步播出,入围第七届戛纳电视剧节最佳长剧集竞赛单元,豆瓣评分高居华语口碑剧集榜榜首。该剧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创作座谈会指出:“《我的阿勒泰》是新时代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为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创作的深厚滋养。”还有评论盛赞该剧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堪称承载着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国产剧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新一笔”。更多媒体报道聚焦该剧IP的文旅“长尾效应”:“马蜂窝平台上,‘我的阿勒泰同款路线’周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75%,北疆环线的自驾在端午热门自驾线路榜单中夺冠。”可以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自亮相伊始就迎来高光时刻,投射出一面既符合当下大众审美偏好又凸显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理想镜像,成为那些深陷“内卷涡轮”中迷惘焦虑一族无限向往的“诗与远方”,为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学IP的创意开发提供了范例。

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书影
一
根据大众文化生产惯例,文学蓝本的艺术水准常常是决定一部电视剧叙事成败的关键。电视剧是最具大众化的叙事艺术,延续了传统说书人的角色,以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或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或反映大时代风云变迁下的世情百态,或书写大众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引导观众从“时代镜像”及“他人故事”中观照自我的位置与处境,为现实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合法化叙述。
小说是电视剧改编的理想文本对象,相比而言,散文的电视剧改编难度偏大,主要原因在于散文以“形散而神不散”为文类特征。其篇章结构相对松散,不强调首尾呼应的情节叙述,也缺乏大开大合的戏剧冲突,尤其是文本中占据较大篇幅的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很难以视听语言形式呈现出来。作为一部由散文改编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提供了颇具创新意识的跨媒介改编实践。此前,根据新疆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散文《永生羊》改编的同名电影被誉为“中国首部哈萨克语同期声彩色故事片”,曾荣膺第七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从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到同名电视剧,这种“可改编性”的根本前提在于原著散文对叙事性的凸显,正如作家李娟本人所言:“文字的精致与精心,倒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原著散文是李娟的“阿勒泰系列”之一,创作素材取自作家在阿勒泰富蕴县的乡居生活。在李娟的散文创作序列中,《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并未被明确标注“非虚构写作”的标签,但是其风格强调创作者的主体介入,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书写日常生活的丰富面向。原著散文包括“记忆之中”“角落之中”两部分,循着时间顺序倒推,以在场者的视角叙述童年成长经历及哈萨克游牧生活。电视剧则从主人公李文秀在乌鲁木齐的孤独闯荡开始,讲述主人公文学梦想受挫后,不得不返回阿勒泰草原与母亲和奶奶相依为命,在夏牧场开小卖部,与勇敢善良的哈萨克少年巴太相爱并决定留在牧场的故事。如何将原著散文碎片化的叙事段落进行拼贴重组,整合成具有内在逻辑和情感线索的故事,这是判断电视剧改编可行性的核心要素。“一个文学改编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故事,它和最初的故事不同,但却焕发出新的生命”,从叙事的意义上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对原著散文的重构与改写,既保留了散文所描写的空间场域与哈萨克游牧生活,又有意识地跳出原著文本的框限,从李娟其他作品(如《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中提炼可供参照的元素,甚至融入了李娟本人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如剧中编辑兼作家刘海波这一形象,其原型被普遍认为是新疆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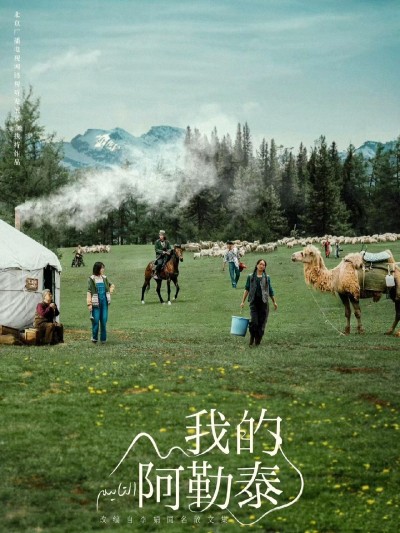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电视剧的叙事惯例需要同其媒介属性相契合,严格意义上不存在散文化的电视剧,那种表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电视文艺专题片,或可原汁原味表达文学蓝本的散文风格,但电视剧无法脱离情节叙事、戏剧冲突和人物塑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剧情设置上可谓别出心裁,戏剧冲突紧紧围绕李文秀和巴太两家人展开,其中前者又穿插进两条情感支线:李文秀与巴太的爱情以及张凤侠和高晓亮的短暂情缘。两个家庭分别代表汉文化和哈萨克文化,关联着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在这一大的叙事框架内,前者还涉及李文秀孜孜不倦追求的文学梦、张凤侠对亡夫的一往情深,后者则融入苏力坦面对时代变迁难以适从的矛盾心态、托肯挑战传统旧俗主动要求改嫁等故事,使得剧情内容饱满、结构紧凑,为电视剧叙事整体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将原著散文与电视剧展开对比分析,就会发现电视剧在个别情节、故事场景及文化符号方面沿用了原著内容:首先,电视剧的“开篇”剧情是对原著“自序”内容的原画复现。原著作者在“自序”中坦言:“无晴无风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通向院门。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然后挖了两三米就没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这段文字交代了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再现了北疆冬日寒冷孤寂的居住体验,具有很强的画面感。电视剧“片头”对这一描写片段进行了视觉还原,先是以空镜头拍摄风雪中的小卖部,风刮得小卖部的旧木牌呼呼作响,接下来采用移镜头表现大雪堵门的自然环境,画面舒缓展开,配以主人公的独白,“在大雪围拥的安静中,翻开文字……”电视剧以倒叙方式从文本书写的字里行间,追溯主人公经历过的那段贫穷、虚荣、热情、带有自卑却又滋味无穷的少年时光。
其次,电视剧善于捕捉原著中描写的日常生活细节,借以触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例如,原著以幽默笔法提到了“我”从乌鲁木齐买回不断长肥的“袖珍兔”的故事,电视剧也出现了这一细节,只不过故事发生地点由乌鲁木齐变成了某县城。原著有一篇散文名为《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描写了一个颇具镜头感的场景:“我不小心在这样的风里失手掉落五块钱,跟在钱后面一路狂追了几百米都没能追上。幸亏钱最后被一丛芨芨草挂住了才停下来。”该场景在电视剧中得到了还原。类似场景还有放烟花、公共澡堂洗澡、乡村舞会、森林里摘木耳、用塑料袋巧妙制作接雨器,等等。
再者,电视剧大量运用原著散文的文化符号,如对日常生活中器物的形象命名,丝布棉布料被称为“塑料的”、相思鸟香烟是“小鸟牌香烟”、木耳被唤作“喀啦(黑色)蘑菇”、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被叫作“砰砰”、孔雀被称为“大尾巴漂亮鸟”。原著散文这样表现母亲这一形象的机灵聪慧和善于应变:“在汉语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电视剧中张凤侠则犹如一位操持话语转换密码的魔术师,她深谙草原游牧生活规则,擅长以生动具体的话语表述填补语言沟通上的困境,赢得了哈萨克牧民的信赖和尊重,有效实现了由“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视角转变。此外,电视剧大量运用原著中提到的民俗文化元素,凸显影像的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色彩。如对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干奶酪、包尔沙克、葡萄干儿、杏干儿、馓子、塔尔米、馕块儿),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如阿肯弹唱会、叼羊、赛马、驯鹰,还有哈萨克传统婚礼、宰羊等仪式文化的展示。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后,原著散文采取第一人称视角记录零碎的生活体验,以清新隽永的文字追怀似水年华,侧重叙事写景,较少直抒胸臆或发表议论,其中为数不多的携带哲学意味的文字,为电视剧构设人物关系与叙事框架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原著散文提到“那些猎人和鹰之间,和这片追逐狩猎的大地之间的古老感人的关系,到了今天,真的就什么也不曾留存下来吗?”这段文字既有对传统语境下纯朴生活方式的怀念,也有对现代性及发展主义的反思。当然作者并没有一味沉溺于感伤主义的怀旧情绪,而是以辩证理性的态度对待“变”与“不变”,“古老的弹唱会也在与时俱进地改变着内容和形式”。电视剧瞄准该议题,精心塑造了苏力坦这一形象,他在内心深处固守着对传统习俗的执念,面对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方式显得焦虑不安,在“理想与现实”这对永恒的矛盾之中饱受煎熬,最终通过自我调适,积极转变心态并坦然接受外界事物的变化,苏力坦与巴太之间的父子冲突也得以和解。
整体上看,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吸纳了原著散文的叙事片段、文化符号及空间场域,更为重要的是承继了原著的灵韵(aura)。那是一种内生于北疆草原和哈萨克游牧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远离尘嚣却又并非消极遁世,彪悍血性与善良细腻并举,坚守传统亦能接受新变,偏居一隅却坚持传承真善美。李娟散文的这种精神气质赋予了电视剧某种诗化品格,以一种舒缓、清新、自然,契合于哈萨克牧民时间意识的叙事节奏展现日常生活的微观细部,反映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将以苏力坦为代表的哈萨克牧民在走向现代生活旅程中的心理起伏和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概括和凸显了电视剧的主题意蕴,有助于激发观众的“情绪共鸣”,“每一种表现形式都带有面对面交流的痕迹,而且每种形式都曾从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中嬗变而来”。
二
《我的阿勒泰》与常规意义上的电视剧叙述语法存在明显不同,尤其注重布光、色彩、声音等视听语言元素的协调搭配,特别关注画面质感,成功构建起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共同体叙事与共同体美学。
第一层次是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体验中,哈萨克族与动物和草原建立了亲密关系,这种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深厚情谊甚至超越了人类之间的情感。电视剧第三集出现了“树梢悬挂马头骨”的段落,女主人公李文秀对这种仪式文化并不了解,存在认知层面的隔膜,后来巴太以他对“踏雪马”无微不至的关心,为李文秀理解哈萨克族的生态观提供了教科书式的指南。对哈萨克牧民来说,马是最亲密的伙伴,马死以后,主人会将马头骨挂在树上,以便牧归时能够远远看见马,正如巴太所言:“没有巫术,只有怀念!”第八集的“荒野追逐”片段是对西部片叙事程式的再现,也呼应了中国古装武侠片的经典场景。李文秀遇到高晓亮在牧场行骗,紧急关头她骑着“踏雪马”去追赶高晓亮,“踏雪马”因受猎枪惊吓撒腿狂奔,李文秀在惊恐万状中被甩下马背,危急关头巴太为救李文秀不得不选择射杀“踏雪马”。电视剧此处采用极富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画面构图,镜头由远及近,远景中人物所处的环境被处理成暗红色:血色天幕,暗红的背景及侧景,世界仿佛瞬间被涂抹了浓重的血痕……为了减轻“踏雪马”垂死挣扎的痛苦,巴太忍痛结束了马的生命,镜头推进,以特写镜头凸显巴太因极度痛苦而扭曲的面庞,他在绝望中割下马头绝尘而去,声嘶力竭的呐喊声在草原久久回荡。演员在此处的表演极富穿透力,情绪变化把握得恰到好处,也给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剧情演绎至此,观众或许会质疑巴太对李文秀的感情,认为在巴太心目中,“踏雪马”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重要性超越了爱情。这种认知显然有失偏颇,未能结合游牧生活方式去思考哈萨克族对马、羊之类动物倾注的特殊情感——那是一种超越表层功利,历经生产生活的千锤百炼构建起的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哈萨克族遵循“牛羊依靠草地,牧民依靠牛羊”的朴素信条,明白“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的生存道理,采取转场放牧的方式,让草原定期休牧,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电视剧第八集有一段关于张凤侠与李文秀的母女电话交流,张凤侠凭借其对哈萨克游牧文化的理解,回答了李文秀关于“那仁牧场好,为什么还要转场”的疑问,答案就是要让草原休息。这种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与以高晓亮为代表的利欲熏心的盗挖盗猎者,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照,具有指向鲜明的现实批判意味。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层次是表达新疆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守望相助、情感互嵌、文化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传统意义上说,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其空间意识和场域观念更显流动性。在这种冬夏转场的流动空间中,《我的阿勒泰》将剧中人物张凤侠经营的小卖部设置为矛盾冲突交汇的“共用空间”,小卖部也是夏牧场上人们交往交流的互嵌式场域,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和折射情感变迁的重要作用。“整个空间,或者空间的碎片,都不是一个社会文本,它本身是特定文本的语境”,小卖部汇集了油盐酱醋等日常必需品,人们赶往这里采购生活物资,同时也交换各种新闻或小道消息,赋予了小卖部信息集散地的特殊功能。在茫茫的阿勒泰草原上,小卖部充分发挥其联通职能,将四处分散的牧民个体整合为相携互助的草原游牧群体。此外,小卖部拥有一部无线座机电话,这一现代媒介在夏牧场显得另类而稀罕。无线座机电话不仅是张凤侠外出办事随身携带的装扮标配,也是远离繁华都市的牧民们联系外界、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窗口,表征着现代生活方式对牧民传统习俗的影响。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和彰显,并没有停留在简单刻板的宣教层面,而是遵循文艺作品的审美规律。“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土壤和根基,培育出斑斓多姿的文化百花园,形成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的整体图景。《我的阿勒泰》遵循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原则,没有脱离实际将共同体意识书写为一种乌托邦想象,而是诉诸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借助文化误读乃至观念冲突的有效消解,构建起一种契合时代语境的共同体叙事。这里有两处剧情值得着重分析:一是张凤侠一家与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对转场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在牧民的常识系统和日常观念中,转场是十分重要的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传统节日,转场出发时,牧民要身着盛装,举行庄重的仪式祈祷转场顺利。张凤侠是从内地来疆的支边青年,对转场的文化意义知之甚少,根据农耕文化思维认为长途跋涉不适宜穿戴好衣服。当转场的队伍经过护边员朝戈家的蒙古包时,朝戈奶奶认为张凤侠这些外地人穿着太过随意,并且颇具哲理地指出“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这种游牧生存智慧无疑为张凤侠一家提供了调整文化认知以适应草原生活规则的理想镜像。二是苏力坦的大儿子木拉提之死及其导致的后续反应。木拉提常年酗酒,与妻子托肯貌合神离。木拉提在一次醉酒后冻死在雪原,电视剧以大俯拍镜头呈现木拉提的周年祭场景,李文秀因为不了解哈萨克族“必须还完债才能安息”的习俗,自告奋勇拿着账本四处寻找牧民要债,在周年祭追索木拉提欠下的两千多元债务显然捅了马蜂窝,苏力坦一家悲愤交加,对张凤侠母女充满怨恨。此处也有一段“荒原追逐”叙事,巴太携带弓箭纵马追赶张凤侠母女,场面气氛极其紧张,就在观众以为巴太气势汹汹前来“报仇”之时,剧情得到了突转:原来巴太是受父亲苏力坦之命前来处理木拉提生前欠债一事,他坚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有现金,就拿骆驼抵债。张凤侠在与牧民的长期交往中锤炼出了一套生存法则:“他们(牧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因此,当巴太到小卖部询问哥哥木拉提是否答应过托肯要离婚的事时,张凤侠的回答非常果断:“没有!”她没有因为感同身受的“姐妹情谊”而撒下“善意谎言”,这种恪守事实真相的处世态度貌似生硬,实际上却体现出尊重规则的大智慧。这场误会的化解既褒扬了哈萨克牧民坚持诚信的美好品格,也启发了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中将心比心、彼此映照、平等对话,这也是从文化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应当说,《我的阿勒泰》交织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和声,围绕共同体叙事这一核心指向,张凤侠心甘情愿驻守在彩虹布拉克,李文秀深思熟虑后愿意放弃到北京寻求文学梦想,选择继续留在牧场……剧中几位年轻人的跨族际爱情和婚姻,如护边员蒙古族小伙朝戈与托肯、朝戈哥哥与北京本地人、李文秀与巴太,均以真实可信的个案,为讲述新时代的共同体故事提供了鲜活素材。
电视剧叙事的灵魂在于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我的阿勒泰》的共同体叙事密切围绕几位典型人物推进,借助戏剧冲突和细节展示勾描人物的立体化性格特征。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着重塑造了李文秀、张凤侠、苏力坦、巴太等典型人物,有的可以在原著散文中找到原型,有的纯粹是因剧情需要予以添加,但不管如何,这些人物形象贴近生活,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成功的人物塑造就是要表现出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样态。
李文秀这一形象源于原著散文的叙述者“我”,糅合了作家李娟的人生经历。电视剧开篇,李文秀漂泊在乌鲁木齐一家餐厅打工,“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那么多人,充满着生活的无数种可能!”她梦想成为作家,聆听了作家兼出版人刘海波的讲座,讲座题目《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学创作谈》既明确表达了“文学源于生活”的真谛,也渲染了电视剧叙事的现实主义总基调。针对李文秀提问“到底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刘海波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写作训练的路径:“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李文秀带着刘老师的忠告和指导,回到打工的餐厅,不出意料再次遭到同事的嘲笑戏弄,并最终因工作失误被辞退。虽然作家之梦道路坎坷,但她义无反顾地在“上大学”和“记录自己的生活”之间选择了后者。李文秀从乌鲁木齐返回阿勒泰,提供了一个观照牧民生活的外部视角,电视剧在叙述李文秀辗转回到彩虹布拉克时,场面调度启用了画框意象,张凤侠用石块垒成电视屏幕造型,以此抚慰吵闹着要看电视的奶奶。李文秀走到石块垒成的电视屏幕画框中,以“镜中人”的姿态与张凤侠及牧民们再度相遇。李文秀在适应阿勒泰乡村和牧场生活时,经历了一系列文化误读乃至观念碰撞,最终通过与巴太相爱,与牧民共同劳动共同娱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那股流淌在夏牧场的人性之美。她接受了哈萨克牧民日常交往的心灵规则,在“生活世界”与“写作世界”之间找到了平衡。有意味的是,《我的阿勒泰》以李文秀不懈追求作家梦为线索,触及了“性别与写作”等深度命题,强化了影像文本的社会文化意涵。电视剧第三集有一个片段,讲述刘海波慧眼识珠,发现一名颇有文学天赋的中年女士,他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鼓励她坚持创作,这位中年女士虽然对自己的文学才华被伯乐发现而受宠若惊,但思量片刻还是选择放弃文学梦想,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电视剧特别安排李文秀与伍尔夫画像的两次相遇:第一次是李文秀匆匆赶到会场听讲座,途中看到了这幅画像。第二次是李文秀被酒店辞退后再次来到讲座会场,在楼梯口看见这幅画像并停下来将其扶正。《我的阿勒泰》在剧情中加入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画像,旨在激发观众对于女性写作的思考,强调女性要争取独立自主,要敢于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张扬主体性。
张凤侠的形象可谓圈粉无数,她乐观开朗、敢爱敢恨,追求浪漫但又脚踏实地。其性格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一是重情。为了实现“找个最美的地方,让丈夫住下”这个愿望,她果断决定跟随牧民转场,并且坚持要走最危险的“仙女湾”,只因为那里是她和亡夫初次相识的地方。二是善良。她热情坦率,对待牧民如自家兄弟姐妹,闲时与哈萨克妇女们用方言闲聊、嗑瓜子,牧民到小卖部赊账成为常态。她孝顺婆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坚持把婆婆带在身边照顾。她义无反顾支持女儿的写作事业。即使对待狡诈阴险、唯利是图的高晓亮,她也真诚告诫对方:“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些卖假虫草的人混在一起!”三是诚信。当高晓亮背信弃义、携货潜逃后,张凤侠宁愿自己吃亏,也绝不损害牧民丝毫利益,硬是自掏腰包向牧民支付了做黑药皂的工钱。张凤侠从内地支边到新疆,数十年的北疆草原生活让她对这片土地充满深情的眷恋,她选择继续留在彩虹布拉克开小卖部,成为协调草原牧民日常关系、守护游牧人群生存法则的重要主体。
苏力坦和巴太这对父子之间由冲突到和解的剧情布设,是《我的阿勒泰》又一叙事亮点。作为老一辈牧民的代表,苏力坦习惯于传统的狩猎、驯鹰和游牧生活,他固守旧的传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相对迟缓,虽然同意儿媳托肯改嫁,但要求不能带走孩子。他希望巴太能够子承父业留在牧场,因此千万百计阻止儿子回马场工作。苏力坦与现实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他本人所言:“难受,喜欢的生活像消失了一样……枪没了,转场不再走仙女湾,儿子不再放牧……”经过艰难的心理调适和思想斗争,最终苏力坦以“爱”的名义坦然接受了外部世界的急遽变化,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
三
新疆的地形特征被形象地概括为“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成为新疆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地理符号。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中提炼审美意象,化入诗词歌赋与绘画影像,为“大美新疆”的区域形象传播提供了理想载体。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因昆仑神话和昆仑精神而声名远播,成为具有中华文明探源意义的地理符号表达。天山在古典诗词、王度庐小说以及还珠楼主、金庸、梁羽生的武侠世界中被反复书写,2013年新疆天山“申遗”成功使其声名更甚,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疆地域形象的代名词。阿尔泰山旧称“金山”,因自然风光旖旎、矿产资源丰富,历史上是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汇之地,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以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山三条逶迤绵延的山系为地理坐标,连接起点缀其间的戈壁、沙漠和绿洲,形塑了新疆特有的风景美学。近年来,随着文学作品《本巴》《西长城》、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平凡英雄》、电视剧《沙海老兵》《阿娜尔罕》、舞剧《五星出东方》《张骞》、杂技剧《天山雪》、舞蹈《阳光下的麦盖提》《爷爷的萨玛瓦尔》、MV《天山放歌》等一批文艺精品力作的创作与传播,新疆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斑斓多姿的风景美学成为具有高标识度的文旅符号。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高品质的画面构图和多向度的风景展示,将原著散文所要表达的“世界温暖,草原明亮”的情感基调具象化,致力于寻找北疆草原和阿尔泰山的“如画美”,在审美效果上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
首先,作为一个重要的风景美学概念,“如画的”(picturesque)起初“并未特指风景,而是意指某种景色或人类活动适合入画”。究其含义,是指“每种景色从题材和构图方面来看都可以满足某种图画性的描述”。风景的呈现依赖摄影机的框定,文化生产者决定着哪些风景元素可以“被看见”,哪些风景元素或可被忽略,因此影像展呈的画面是经过精心构图和严格剪辑之后的成品。《我的阿勒泰》对哈萨克牧民转场的视觉再现最具代表性:摄影机运用远景镜头拍摄转场的壮阔场面,远山淡影和万马奔腾等环境景物占据主体位置,随后以中景和近景表现转场队伍的磅礴,配以舒缓的插曲及背景音乐,带领观众近距离欣赏了一幕反映转场的流动的民俗文化盛宴。第七集开篇有一段经典的风景再现,画面采取常规构图,布光及色彩柔和,远处皑皑雪山、近处的白桦林及如茵草场,草场上悠悠走过的羊群,牧民日常生活细节与唯美的自然景观融汇在一起,具有油画般的质感。电视剧将这些表现风景的段落放置在每一集字幕出现之前,在叙事意义上发挥着连贯各集内容的作用。
其次,《我的阿勒泰》坚持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影像呈现高度契合剧中人物的生活体验,拒绝虚构一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幻境,借助巧妙的艺术构思与审美表达,在推进“崇高美”与“牧歌美”的融合方面迈出了创新步伐。在大众关于阿勒泰草原、牧民转场和阿尔泰山的文化想象中,黛青色的群山、浪漫的白桦林、浅唱低吟的额尔齐斯河、醉归的哈萨克牧民、热情奔放的乡村舞会……这些都是常识性的景观元素,但《我的阿勒泰》并没有放大常识性符号以迎合大众的审美偏好,它坚持透视生活的本真状态,试图构建一种“崇高美”和“牧歌美”交融的视觉美学。“风景意义的崇高美须有危险的、令人敬畏、给人激励的美景,特别是得有荒凉的山景。”在“如画美”的话语系统中,“崇高美”既指向一种由险峻山峦(如阿尔泰山)带来的居高临下的畏惧感和威严感,也指向一种由艰难万状中求得生机的特殊体验。原著散文中有一段描写主人公一家随牧民搬迁到沙依横布拉克夏牧场的文字:“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女人就这样被扔在暮色中的荒野沼泽中。”初到夏牧场的体验并非田园牧歌,四处布满沼泽地,帐篷顶被风刮跑,一家人半夜爬起来追赶屋顶。此外,电视剧的前半部分在表现彩虹布拉克的环境状况时,影像画面的色调以昏黄为主,画面中的意象极易使人联想起“荒凉”“孤寂”“寥落”等形容词。电视剧的后半部分将空间场景转移到夏牧场,画面中的景观元素参差多变,显得丰富多样又充满生命气息。《我的阿勒泰》对牧歌美的展示,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夏牧场如画风光的再现,而是将触角深入牧民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塑造出以巴太为代表的牧民纯朴善良、热爱生活、尊重大自然的优秀品质。“人在旅途,不论是乡村风景,还是乡民性格,它们展现出来的原始质朴迷住了游客。”与此同时,电视剧对以高晓亮为代表的世俗、狡猾、善于伪装和表演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展开了犀利批判。
最后,《我的阿勒泰》对“如画美”的追寻离不开网络视听媒介的技术赋能。该剧由中央电视台和爱奇艺联合出品,近年来爱奇艺等网络视听平台抢抓机遇,聚焦时代主题,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推广应用媒体技术变革成果,制作出《长风渡》《宁安如梦》《平原上的摩西》等优秀作品。“爱奇艺基于经典小说、剧本、历史资料等专业内容构建垂类知识库,并投入技术和业务力量进行研发训练,形成自己的影视文学大模型。”爱奇艺秉持“内容为王”的基本原则,注重将创新思维注入剧本创作,以高质量文学蓝本推动优质剧集的生产。爱奇艺还特别强调技术赋能,在拍摄剧集《我的阿勒泰》时,“采用了‘制作上云’的先进技术方案,样片通过专用的DIT工具上传至云端,并在制片管理系统中实时更新,主创在云端即可查看、搜索和分类素材,大大提升了后续的剪辑效率”。此外,该剧采用音画同步的方式,片头曲《阿勒泰》和片尾曲《回家吧》《彩虹布拉克》《苍茫的凝望》《月光》等,歌词中出现“苍茫”“辽阔”“草原”“马儿”“沙漠”“冬不拉”“毡房”“牧场”“驼铃”等富有边地风情的词汇,曲调彰显民族民间音乐风格,一方面呼应了影像的主题表达与审美风格,另一方面有助于调动观众关于乡愁记忆的情感共鸣。上述因素协同联动,为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成功制作与有效传播奠定了基础。
结语
综而论之,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创造了优秀文学IP改编为影视剧的成功范例,再度反映出文学经典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兴盛的语境下,其扎根大众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透视社会复杂面向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审美精神的不懈追求,为影像文本注入了特定的神韵和气质,其艺术功能甚至超越了情节叙事与人物塑造,有效实现了媒介互动格局中传统文学文本的“破壁”与融合,激活文学作为生产要素助推文旅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能动性。此外,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并未沉溺于过度渲染北疆草原的田园牧歌之美,它追求清新质朴的视听语言风格,凸显崇高美与牧歌美的深度融合,创造了一种契合新疆地形地貌、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的影视审美样式。一般认为,优秀文艺作品是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的重要载体,文学、影视、音乐、歌舞、绘画、雕塑、曲艺、杂技等在建构新疆区域形象、展示新疆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传播富有现代意识的新疆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成功实现了粉丝经济与旅游经济的互促互融,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文化润疆”工作贡献了文艺力量。
*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资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文化润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JJDM0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第二批)研究课题资助项目。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邹赞 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7期(总第106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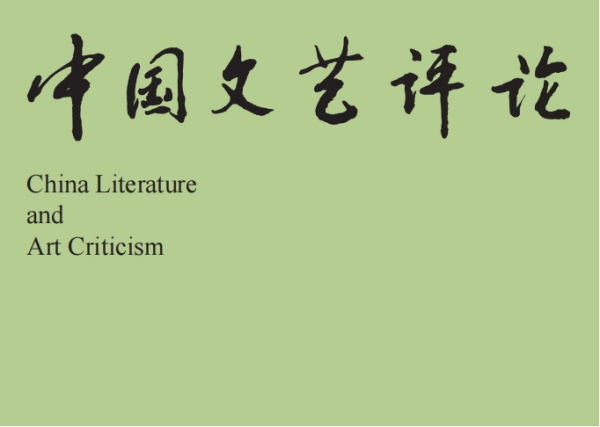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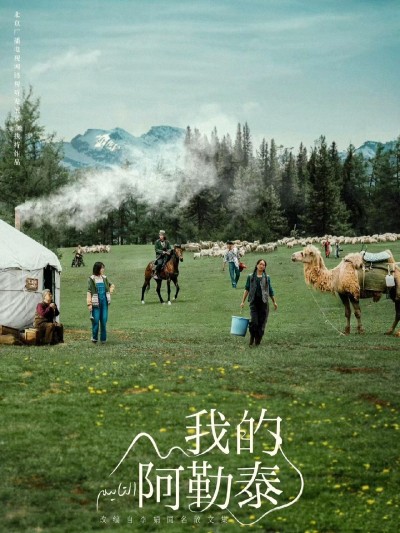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