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旁观者”的生存哲学
——读杨争光《我的岁月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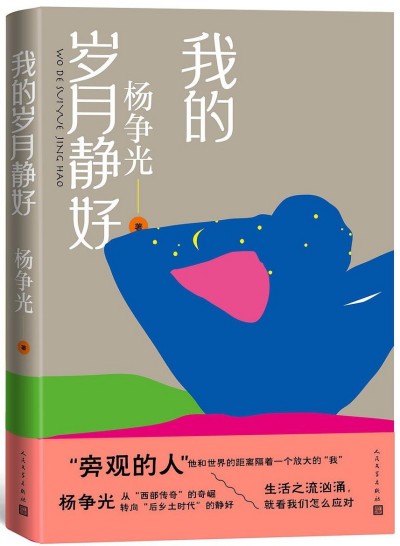
写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意味来,写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生存哲学来。《我的岁月静好》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篇幅不长,却写出了当今社会中的人们对生存哲学的探寻与追问。
尽管对于杨争光,从其人到其诗歌、小说、影视,我算是很熟悉了,但他的每一部新作又都有让我感到陌生的东西。最近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我的岁月静好》,自然保持着他从诗歌写作中一直延续而来的语言的机敏、灵动和缠绕术。但其中呈现的他的生存状态及其感悟,却迥异于他在《老旦是一棵树》《公羊串门》《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中的那种寓批判于荒诞的态度和写法,而开始进入对日常生存的哲学体验。
《我的岁月静好》最让我关注的是他对一个旁观“旁观者”的立场,以及那句被他激活了的关中人的口头禅“噢么”。小说呈现出的全部生存哲学都是建立在“旁观者”和“噢么”之上的。
小说从腰封到内文都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可以避免生活的很多烦恼。”这句话暗示出了作家自身作为“旁观者”的主体立场,并有效地将其从“我”这个表面上的叙事主体中抽离出来,也从杨争光本人的生存体验中抽离出来,使其得以平静地去“观赏”自己在小说中展示的日常人生。这种让自己看自己“演戏”的体验,或许就是杨争光感受到的“岁月静好”吧?而这种生存状态和人生态度就隐含在一声“噢么”之中。
小说用杨争光惯用的诗化语言呈现出了故事中的“旁观者”形象——一个叫“德林”的“我”。这个“我”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清醒、理智和不动声色。很显然,正是这种“旁观者”态度使德林始终感受着“岁月静好”的生存体验。有趣的是,作为这部小说的作者,杨争光既是这种“岁月静好”的体验者,更是小说中这位旁观者的旁观者。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才凸显了套封中所说的“他和世界的距离隔着一个放大的‘我’”。
值得关注的是,杨争光在这部小说中已经远离了他曾经书写的荒诞而奇崛的特殊生活(如怪诞的历史或者传奇的现实),而是回到了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中同样怀有仇恨的“老旦”(“我”爸)最终没能变成一颗树,而是无奈地装病住进了医院。而这种回返并不意味着杨争光从浪漫回到了凡俗,反而是让他从对日常生活的凡俗体验上升到了哲学。小说以一种叙事缺陷的方式告诉了人们这种哲学来自老庄。从小说的叙事策略而言,这个思想的谜底是应该由读者来揭穿的,但他既然已经自己暴露了,那也就更加明确了人们对这种哲学的判断。事实上,老庄的道家哲学中本来就有这种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态度,以及超然物外、反观自我的智慧。所不同的是,杨争光将这种哲学与德林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情绪联系在一起,并加入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阐释。杨争光依托德林,认为老子《道德经》种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是不想仁慈,而是因为无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是不愿共情,而是因为共情容易成为滥情,于人于己无益,反倒有害”。因此,人不应被情感所绑架,也不应为利害所困扰,而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于是,无论遇到天大的事,好事或者坏事,均可用一声“噢么”了事。
小说中,杨争光借用德林的口说:“有人说,这样的经验主义是动物主义。//我更愿意承认经验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因为经验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实用,不追逐甚至反对粗线条的宏大叙事赐给自己虚幻的兴奋。”由此,他推祟的是实用主义,他认为鲁迅写了那么多“世界的残缺”“人性的扭曲”,却最终写不出怎样活着才是“好的活着”,因而是“绝望的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向往的“岁月静好”实则是对理想、对完美、对诗意的放弃,是对现实、对残缺、对日常的妥协。然而,这种生存哲学却又不是一般意义所说的消极的人生观。在小说中,德林明确说,他是在认真工作,潜心读书,并保持着“静好”的心态。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哲学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是解开这部小说的密码所在。小说所渲染的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对于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来说,都在于对经验中形成的习惯的认可。而作为一个诗人和能够去写作“岁月静好”这样的小说的作家,却又对这种习惯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警觉,其写作的意义恰恰在于对这种习惯的逆反和破解,在于惊醒在这种习惯中麻木而不自知的“二哥”“我爸”“我哥”和“我弟”们。由此,我认为,小说所渲染的生存哲学,既不是完全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也不是完全的老庄哲学,或者鲁迅式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而是保有理想的实用主义,或者基于实用的理想主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把握小说中反复被马莉质疑的那几个关键词了。如德林被马莉指责的“自私”,其实是一种“自在”;“冷漠”,其实是一种“冷静”;“理智”,其实是一种“理性”。还有“遗忘”,特别是指那种“选择性遗忘”,其实是一种对残缺的包容;“隐忍”,其实是对“静好”的一种向往等等。
熟悉文学写作的人都会知道,传奇与玄幻的东西,或者宏大的历史叙事,其实都不意味着写作的难度。写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意味来,写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生存哲学来。《我的岁月静好》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篇幅不长,也不够惊心动魄,却写出了当今社会无数麻木于习惯之中的人们,困扰于无奈之中的人们,对生存哲学的探寻与追问。而这个,才是难度。
(本文作者:李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书籍作者:杨争光)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