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作者感言
美学的文献与艺术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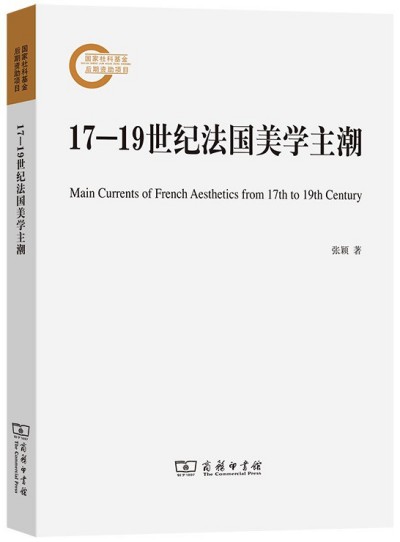
感谢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授予《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这部著作为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一部基础理论研究能够获此殊荣,身为一名美学研究者,一名宽泛意义上的“理论工作者”,我倍感荣幸与欣慰。
这本书的写作正式开始于2015年,历经6年完成。我在《后记》中坦承道:六年光阴,远不足以道尽这段美学故事;纵然竭尽全力,至多粗笔描摹大概;但我依然希望,这本小书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讨论起点。
我想借此机会稍作说明:这里说的“新的讨论起点”,也是我结束本书写作后的两个新的努力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文献框架的继续搭建,译介工作的持续进行。
在理论领域,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问题域,其成熟的标志,往往是研究者们对于基础文献的基本共识。我们知道,相比于德国古典美学,相比于20世纪法国理论,法国17—19世纪的理论几乎不曾占据过“显学”位置,甚至其理论的体系性本身一直被存疑。在我国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国际成果,我钩沉出29部一手文献,精心拟定了一份共计25位法国美学家的名录。这个文献框架能够扎实地证明一个宏观结论:法国三百年现代美学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该体系的核心议题是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古今之变”,每一部主要文献都围绕这个议题试图做出回应、推进或者调和。
在这份25人名录中,仅有7人的著作拥有中译本,这说明译介的工作任重道远。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需要优秀的外译成果;认识西方文明的真面貌,也需要可靠的汉译工作。我自己也在从事相关文献的翻译。文明互鉴,有赖于译介者一字一句精细如发的穿针引线;一经翻译和传播,西学精华将更容易吸收、落地,化为我们自身的学术给养。我热切地期待全部这些文献获译,到那时,该领域的研究必将兴旺起来。希望我的这本小书可以充当一个讨论的靶子(那真是太荣幸了),也希望我届时能有机会像笛卡尔那样做出反驳与答辩,有机会借鉴真知灼见来修正我的观点。
第二个方向,是从美学史向艺术理论史的延展。
艺术理论被建设为学科,是我国的一个突出特色,也是我国的学术优势。在2022年新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里,不再使用“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名称,代之以“艺术学”,更重要的是名称后括号中的文字,它们清楚地表明这门学科的属性,即源自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性、涵括史论评的全面学理性。艺术学理论曾被某些考研机构宣扬为“最容易跨考的艺术学专业”;改称“艺术学”后,它的跨学科特质得以保留,难度则明显增大。换言之,艺术理论有其植根于实践的独立特性,很难直接被美学理论简单框限。
在前述那份29部文献里,有不少切中美学议题的跨界文献,比如夏尔·巴托那部以“美的艺术”概念著称的著作。(这部1746年的艺术理论著作,直至2015年才拥有第一个英语全译本,2022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一个汉语全译本。)我准备以这套美学文献为初始位置,一方面将其中的艺术哲学论题深化和系统化,一方面以此为契机,扩展文献群。目前,我整理出的相关艺术理论包括美之学、摹仿论、诗如画、形与色、情感论、表现论六大议题。
我力求挖掘艺术理论的一般规律,但相较于美学体系,艺术理论的体系性更难把握。美学扎根于既有的哲学,在面临新的艺术现象时,常会有一种有限感,被催促着创建新理论、走向新感性。艺术理论则不同,它完全可以始于复杂丰富而充满未知的实践,拥有未可限量的创造力和活力。不管是站在艺术门类内部还是宏观的外部去做观察,我总感到视野里仍有一大片迷茫世界。我们至今还在为艺术的边界争论不休,也时常为新的艺术形态而苦恼或兴奋。或许可以这么说:艺术学的体系,未必如美学那样须待渐老渐熟,而更多地以非规范性为特征,自身含有一种破旧立新的巨大动能。这便要求我们在钻研艺术理论时,尤其不应停留于对现成规范的整理与认定,更应当立足现象,尊重创新。
总而言之,理论研究,既需要宏观上的视野,也需要抠文献的韧劲、磨翻译的耐心,更需要时刻准备做出质疑与反思——包括自我质疑和自我反思。我认为,这也正是“啄木鸟杯”所倡导的啄木鸟精神——向上、执著、认真、专业。

(作者:张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副主编)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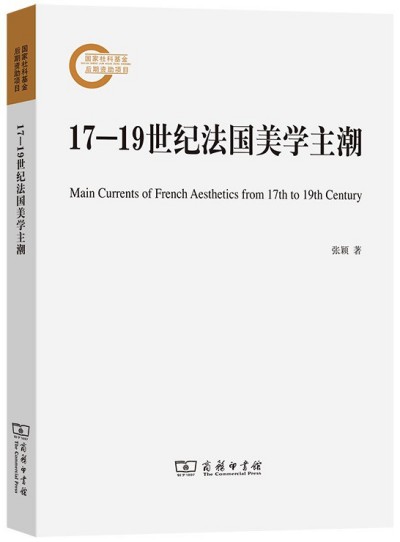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