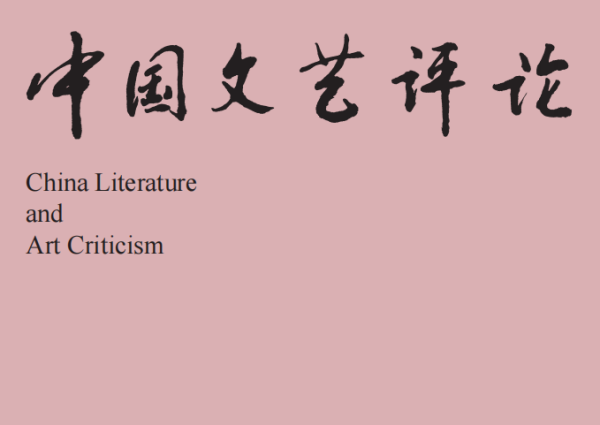
【编者按】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文艺与文艺批评肩负着构建中国话语、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互鉴的特殊使命。本期专题邀约中西学者,聚焦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艺与文艺批评,“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特别关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汉学思想”主导下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当代诗歌海外传播的现状和紧迫性等命题,从“中国经验”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重新审视多元语境中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探讨中国文艺及批评“走出去”“走进去”、主动有效地走向世界的路径。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开始在国外得到接受并产生愈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一方面得助于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者以及一些知华友华的汉学家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本土文艺批评家和学者也开始直接用外语撰写评论文章或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频频亮相,并取得了同样明显甚至更为直接的效果和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要想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就得首先走向英语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倚重国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努力外,中国本土的学院派批评家也应具备直接用英语著述的能力,或借助翻译的中介在国际主流文学艺术研究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样才能主动地走向世界,而不是等待国外汉学家来“发现”自己或译介自己的著述。本文试图与广大批评界同行分享这方面的成败得失。
【关键词】中国文艺批评 当代 英语世界 汉学 批评阐释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在全世界的接受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愈益得到国内外文艺理论批评界的认可,这一方面得助于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者以及一些知华友华的汉学家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本土文艺批评家和学者也开始直接用外语撰写评论文章,或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同样明显的效果,并产生了愈益广泛的影响,这其中英语世界的重要中介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们都知道,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旅行工具的更新和互联网的连通作用,传统的时空观念已经大大压缩,几十亿人生活在地球上就仿佛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里,来自不同民族/国别的人们彼此相互依附、休戚与共,从而使得美国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构想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日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方面,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本土批评家积极介入理论争鸣
我们经常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用英语撰写出来发表在诸如《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细胞》(Cell)等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上。最近,我们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成效中也发现,实际上,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也应该是无国界的,只是文学艺术的传播更加倚重翻译的中介,这方面批评性的讨论也起着重要推介作用。笔者在此欲将一句常为人们引证的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稍作一些修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出自鲁迅的一句名言,但是据专家多方考证,鲁迅的原话并非如此,他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笔者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越是容易彰显其独特之处,从而也就越是容易被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看重。但是这却离不开翻译的中介。如果没有翻译的中介,也许会是另一种相反的情形: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反而越是难以走向世界。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1924-2019)曾在20世纪80年代直言不讳地说过:中国作家为何长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优秀文学翻译的缺席。在他看来,如果当年鲁迅的作品拥有优秀的翻译加以推广,鲁迅也许早就问鼎诺奖了。笔者在此用一个成功的例子再作一补充说明: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为何能获得诺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的无与伦比的翻译,他们分别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以及诺奖评委的母语瑞典语重新讲述了莫言小说中的故事,从而使得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和理解他的作品,同时也使得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读到莫言的作品。再加之一些在海外工作的华裔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批评性推进,也使得莫言进入了当代英语世界的学院派批评家的视野。语言的障碍一旦消除,作者与读者—批评家之间的距离也就大大地缩小了。当然,我们在借助英语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国际汉语教育,使汉语早日成为其广泛影响力仅次于英语的世界主要语言。但是,在这一目标尚未实现时,暂时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来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和紧迫性。
当然,如果我们仅限于文学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说,翻译只是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在海外接受和传播的中介之一。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些仅仅取悦普通读者的畅销作品并不缺乏翻译,一些国外出版商甚至不惜代价购买版权,并且开出高价邀请优秀的译者来翻译他们的作品。但为什么这些作品很快就成为了“过眼云烟”呢?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文学批评对于一国文学在另一国或另一个文化语境中接受和传播的重要作用。在笔者看来,一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经典,除了翻译和改编的重要作用外,还取决于另外几个因素,其中理论批评与阐释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试想,如果一部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学批评界无声无息,那么就说明这部作品在另一语境中仍然处于“死亡”的状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就不难给出解释。由于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因此在本文中多以文学批评作为个案。为了使本文观点更有说服力,笔者主要列举本人所从事或直接主导并参与的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次国际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论争作为个案。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关于“强制阐释”现象的批评和讨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中国的学院派批评家张江。这个话题也是张江经过多年的思考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话题,因而一经译成英文以及其他主要语言就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另外张江本人也不满足于这个话题仅仅在国内产生影响,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开阔的国际眼光和跨文化意识,主动地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所瞄准的对象并非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外汉学家,而是正当红的权威理论批评家。他清楚地知道,要想促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建构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就必须与当今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大家直接讨论和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直接的切磋和对话才能增进与国际同行的理解,最终促进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平等交流和交锋,并就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提出中国理论家的见解。正是本着这一目的,自2015年起,张江先后与欧美多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主流理论家和批评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其中与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 1928-2021)的七封书信往来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往来的书信一下就吸引了英语世界的主流批评家,并且一次性地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第53卷第3期(2016)上,据悉这也是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发表一位中国批评家与西方批评家的多封通信式对话。这一事件已经并仍将继续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该刊主编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是一位知华友华的学院派批评家,长期从事德文和比较文学研究,近十多年来,通过与一些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直接接触,开始关注世界文学语境中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现状,但他也时常苦于自己不懂汉语而不能直接阅读中国批评家和学者的评论文章。所以当他收到这七封信的英译文后,立即觉得这是一个让英语世界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直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很快便决定在该刊一次性地发表这七封信,并邀请笔者为这一组书信撰写了导言。笔者在导言中首先指出:
我们的时代可以被称作“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尽管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处于低谷,但这一趋势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论在其他地方也处于低谷。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各种当代西方文论的浓厚兴趣可以证明这一论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思潮和教义,或者通过翻译或者通过直接引进,均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不奇怪,我的一些中国同仁声称,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患了“失语症”。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在接受各种西方理论的同时,发展了自己对评价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批判性思考和理解,并提出自己的选择。这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试图从中国的和比较的视角出发与那些颇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进行直接的对话。
张江应该说就是这些有着宏阔国际眼光和深刻批判意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这一系列对话中,他凭着敏锐的感觉和犀利的文笔,直接挑战了在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米勒本人也把张江对他的质疑和挑战看作是对他的著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他也认为,通过书信与中国批评家直接对话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他甚至提议将这些书信体对话作为附录收入他的一本中国演讲文集中文版。可以说,张江—米勒对话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极大地超越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和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争鸣:前者基本上是一种“自娱自乐”式的独白批评,几乎未与西方和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后者虽然也引起了西方学界的瞩目,但后现代主义这个论题本身就是西方理论界已有的一个话题,中国批评家所取得的进展只是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批评视角对这一产生自西方语境的批评性话题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并通过这样的直接讨论,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得到国际理论批评界的初步认可。因此笔者从中得出的启示在于:我们过去总是不惜代价地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大家请来中国演讲,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购买这些理论家的著作的中译版权,但却很少成功地推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大家,即使偶尔有幸推介出去了,也很少会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这样看来,米勒与张江的对话便起到了明显的表率作用,其深远的意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彰显出来。
人们也许会问,张江与米勒的对话究竟有何重要的意义呢?笔者的看法是,这两位中西文学批评大家的对话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体现在多方面。首先,这两位批评家的通信往来告诉西方以及国际同行和广大读者,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即使在理论衰落之后的“后理论时代”仍然对西方文论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认真地研读西方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进而从自己的独特立场出发对之进行讨论和批评性质疑;其次,这些书信也表明,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并没有远离文学文本胡乱发挥,而是对照原文仔细研读,从而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再者,这两位批评大家在通过书信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深感中西方学者和理论批评家在一些共同关心的基本理论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和分歧,因此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对话,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直接对话和切磋的方式才能取得更多的共识,并且推进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的良性发展。
毋庸置疑,由张江挑起的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瞩目。国际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时任主编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在得知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后也立即予以关注,并邀请笔者共同为该刊编辑一个主题专辑:“中国与西方理论的邂逅”(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经过精心策划,专辑分别邀请了国内三位批评家就此专题撰写论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先前已经开始的中西文学理论批评对话。该专辑问世后立即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引起了欧美主流文学批评界的瞩目。笔者与该刊主编还特地邀请了欧美学界的三位院士级批评家对中国批评家的论文进行评论,这样便形成了中西文学理论的碰撞和对话。事实证明,这种中西理论家就某一个话题展开的批评性讨论和对话是卓有成效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从中国的视角介入国际性的理论讨论
上面这一案例只是近几年来出现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可惜在西方中心主义把持的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这样成功的个案却十分鲜见。当然,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后看,回顾我们过去的一些批评经验,我们还会发现,一些虽然是由西方理论家挑起的批评性论争,中国批评家照样可以从中国的视角积极地介入其中,并且借机扩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影响力;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于批评的中介,使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引起学术界和理论批评界的瞩目。正如本文一开始就说明的,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受过本科教育后来又在欧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在欧美工作的学院派批评家所起到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们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并在国内大学接受过教育,即使出国留学也依然与国内批评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精诚合作。他们所发表的英文著述大都取自中文原文资料,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批评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仅列举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案例。我们也可以从下面这些论题中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确实抓住了国际理论批评争鸣的热点话题并从中国的视角参与其中、加入讨论,因此客观上也扩大了中国文艺批评在海外的影响。
1.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性问题。这个话题虽然并非十分新颖,但在欧洲汉学界,捷克的普实克、高利克和米列娜,荷兰的佛克马、汉乐逸和柯雷,英国的杜博尼、贺麦晓和曾在英国工作后来回国的赵毅衡,德国的顾彬,奥地利的李夏德,瑞典的罗多弼和陈迈平以及丹麦的魏安娜等汉学家均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结合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实践,从西方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对国内批评家也有一定的启迪。此外他们的批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解构了现代性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为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彰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这些汉学家一直与中国国内的批评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接触,他们或者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或者邀请国内作家批评家参加他们主办的学术会议。在北美汉学界,早期的夏志清、李欧梵、杜迈可等,以及后来在文学理论批评界崭露头角并仍很活跃的王德威、张诵圣、王瑾以及一大批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裔中国学者也都著述甚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旅美学者型批评家刘康同时活跃在中文和英语学界,在一些欧美主流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审美现代性以及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位中国旅美学者型批评家顾明栋也著述甚丰,虽然他的著述大多讨论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或比较文学,但是他在反拨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建构和批判了一种类似“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批评话语,并就此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著述,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但是这方面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尤其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兴起的关于西方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虽然在国内批评界十分红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和批评家,但是在海外却未产生任何反响。挑起这场讨论的两位学者型批评家陈焜和袁可嘉在中国语境中著述甚丰,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他们先后于80年代和90年代出访美国并随后在那里定居,但他们一旦离开了自己所赖以发展成长的中国文化语境,很快就在美国乃至英语学界被边缘化乃至销声匿迹了。虽然袁可嘉去世前依然将自己的著作加以修订并在国内再版,但是他并未有机会就这一话题与美国文学理论界的主要理论家进行对话。这当然与当时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在西方的影响甚微不无关系。虽然笔者于200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试图说服美国同行邀请袁可嘉前来演讲,但他们未查到袁可嘉的英文论文,因而不屑于通过翻译去了解他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看法。这一点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育和启发。
2.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如果说,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主要是在中文的语境下进行的,中国批评家仅发出了一些“独白”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自豪地说,由笔者以及陈晓明、张颐武、王岳川等当时的新锐批评家在中文语境中发起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理论的讨论则首次走出国门,直接进入到国际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发出了中国批评家的强劲声音,并且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在这方面,除了笔者直接用英文著述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外,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汪民安等批评家的著作和论文也通过翻译的中介直接发表在国际主流刊物上,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实验派诗歌等文学流派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从中西比较的跨学科视角论述后现代、后殖民和全球化以及中国现状的著述,不仅在汉学界独树一帜,在国际主流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里克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阐释和运用,具体体现在他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对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后殖民和第三世界批评的质疑和研究。此外,他的学生、新锐学者型批评家张旭东的文艺批评论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1997)也从探讨现代主义文学出发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后现代因素,在同行著述中独树一帜。1997年,张旭东和德里克这两位学者型批评家合作为国际权威刊物《疆界2》编辑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专辑,发表了多位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论文,对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正是从介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开始的。《疆界2》杂志编委、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从西方理论家的视角对中国批评家的论文作了回应,从而形成了中西文艺批评家围绕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这个话题展开的对话。诚然,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这个话题也和现代主义一样,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国际文学批评界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中,中国批评家基本上是“失语”的,尽管中国国内文学批评家发表了大量的中文著述,但基本上未被译成英文见诸国际刊物;而在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则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或者直接用英文著述,或者借助翻译的中介,将自己的观点和批评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甚至直接影响了欧美的主流文学理论批评家,使他们改变了先前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看法。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批评家的努力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载入了两部权威性的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史册。
3. 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建构。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就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交流:一大批在西方学界颇有盛名的理论家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给予了直接的启迪;中国的文化批评家也频频在国际英文刊物上亮相,直接解构了文化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由国际顶级人文学术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推出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专辑在西方主流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越来越为学者们所认识。这部专辑基于在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1995)精选论文,基本上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中西方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除少数文章涉及艺术和电影外,基本上属于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围。美国的两位著名批评家阿拉克和周蕾(Rey Chow)分别应邀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作了点评,并分别从他们各自的西方的和比较的视角与中国批评家进行了讨论和商榷。此外,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家陶东风和金元浦也应邀为笔者主编的英文系列丛书编辑了专题研究文集《文化研究在中国》,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当21世纪初文化研究在西方日益式微时,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应邀来中国访问讲学,通过与中国同行的直接交流和对话,他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长足发展感到震惊,并试图在中国找到文化研究的新的希望。这一切均表明,少数中国学者的批评和研究已经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同步的境地。
4. 文学与影视传媒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当代影视传媒的研究,英语世界的批评界一直有着较大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当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20世纪90年代频频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更是引起了英语世界的文学艺术批评家的关注,同时也围绕他们执导的电影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电影及其批评走向世界要早于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之所以有兴趣翻译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是因为他先看到了电影《红高粱》,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便着手阅读和翻译莫言的小说。在英美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所,比较文学研究曾一度呈危机的状态,因而一批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电影和电视,一些华裔美国学者自觉地运用西方批评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电影,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影响,同时也以中国当代电影的实践和经验直接介入国际电影研究界的一些理论争鸣。在这方面,三位旅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陈小眉曾以《西方主义》一书蜚声国际学界,她充分利用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执教中国文化和文学之便利,十多年前就一直在科伦伯斯举办大型暑期中国电影讲习班,并且邀请中国文化研究和电影评论家戴锦华前去主讲。通过中英文讲演和录像带观看最新的中国电影,美国学生对一些在中国国内也刚刚上映或尚未上映的优秀电影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可惜陈小眉后来离开俄亥俄州立大学,这个项目也就停止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同时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执教的张英进更是公开招收中国电影专业的研究生,鼓励来自北美和中国国内的研究生撰写中国电影方面的学位论文,这对中国电影研究跻身更新后的汉学学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外,他本人也著述甚丰,不断地在英语世界的主流文学和电影研究刊物上发表文章,推进了中国当代电影理论批评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鲁晓鹏主编的专题研究文集《跨民族的中国电影:身份、民族性、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1997)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这本文集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为“民族建构、民族电影和跨国电影”,分别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影的反帝主题和删减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电影以及张艺谋的跨民族电影;第二部分为“港台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政治”,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地区的后殖民性和流散文化主题,并涉及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抗;第三部分为“历史和民族性的出现:跨文化和性别的视角”,分别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视角探讨了陈凯歌、张艺谋等执导的电影的历史和性别主题。鲁晓鹏对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理论深度显然超过一般国内同行的著述。他的这本书已经被很多大学列为研究中国电影的教学参考书。此外,作为一位艺术爱好者和鉴赏者,鲁晓鹏还涉猎中国当代艺术,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著述和文学作品。几年前,他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委托,主编一套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研究的丛书,目前该丛书已经启动,涉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
未来的前景:长路漫漫,未来可期
从上面的简略评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有时还取决于一定的市场所需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则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长久的大计。当年美籍华裔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李泽厚在接受访谈时曾谈到自己在国外的感受,他对包括自己的理论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都充满了悲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好在李泽厚在说上述这番话后不久,他的《美学四讲》就被收入英语世界的权威性文学批评选集《诺顿理论批评文选》,而且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紧接着一大批在英语世界任教以及国内的文学学者就以自己的英文著述在国际学界频频亮相。平心而论,虽然这些少数佼佼者的英文著述与众多用中文发表的当代文艺批评著述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已经开始走向世界,并且率先在英语学界和文学艺术批评界产生了一些影响。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使得原先处于霸权地位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强势,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英语的强势地位和文化传播功能。我们也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要想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就得首先走向英语世界,才能产生国际性的影响。而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倚重国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帮助外,中国本土的批评家也应该具备直接用英语著述的能力,并在英美主流文学研究的刊物上发表,这样才能主动且有效地走向世界,而不是等待国外汉学家来“发现”自己和译介自己的著述。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重视翻译的作用,因为毕竟大多数中国文艺批评家不能用英语著述,在这方面,翻译仍将发挥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国际化的重要作用。我相信,随着一大批在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加盟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将在国际文艺理论批评界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
作者:王宁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1期(总第86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