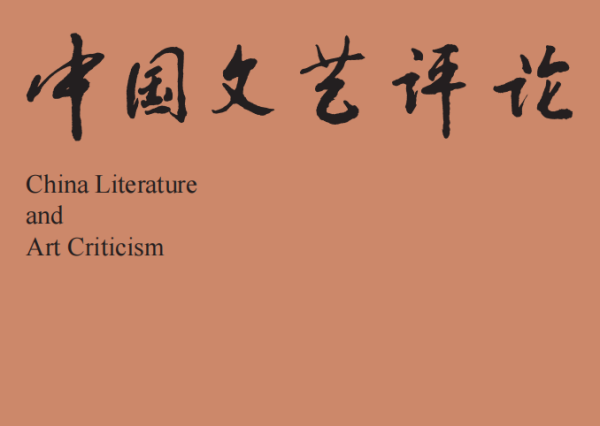
【内容摘要】 兵团文学既自觉融入当代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斑斓图谱,也以反映兵团社会历史变迁和几代兵团人命运故事为旨归,在书写兵团农场日常生活、再现兵团人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心理调适、塑造兵团代际形象等领域取得瞩目成绩。兵团文学具有以奉献精神为内核的崇高美,这种美学特质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此外,兵团文学尝试突破英雄史观束缚,以摇镜头的观视方式,展示兵团人如何重塑“故乡”与“家乡”的情感结构。文本中流淌的乡愁,与其说是对“故乡”的眷恋,不如说是对兵团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叙事文本尝试激活兵团初创期的历史记忆,为弘扬和传播兵团精神、铸牢兵团屯垦戍边文化认同提供重要参照。
【关 键 词】 兵团文学 浪漫的崇高 流动的乡愁 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集“党、政、军、企”等职能于一体,是中国历代边疆治理和中国共产党治疆方略的智慧结晶。六十多年来,几代兵团军垦人扎根边疆、薪火相传,创造出“铸剑为犁”“固边稳疆”的历史伟业,书写出一卷卷金戈铁马、垦荒戍边的西部史诗。兵团文学是兵团屯垦戍边文化的重要表征形式,也是描写兵团人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的艺术形态,成为弘扬和传承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
兵团文学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回应不同历史时期赋予的命题,在思想导向、主题类型和艺术风格上严格遵循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话语,其发展历程也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演进逻辑保持高度一致。兵团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十七年”文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旗帜鲜明弘扬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创办《新疆部队文艺》《生产文艺》《文化生活》《绿洲》等刊物,推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小说、诗歌和纪实文学:小说如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沈凯的《古玛河春晓》、周非的《胡杨潇潇》、权宽浮的短篇小说集《春到准噶尔》《牧场雪莲花》、伊萍的《永远前进》;诗歌如郭小川的《西出阳关》、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东虹的《通往塔里木的路》;纪实文学如艾青的《绿洲笔记》。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除了个别样板戏之外,兵团文艺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是“新时期”文学,见证了兵团恢复建制以来的文艺发展状貌。这一时期的兵团文学以弘扬主旋律为创作导向,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齐头并进,尤其在诗歌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以《绿风》为阵地的“新边塞诗派”崛起,戈壁明珠石河子被誉为“诗歌之城”,推出了杨牧的《复活的海》《我是青年》、章德益的《西部的太阳》《五四之歌》、洋雨的《丝路情思》、杨眉的《雪山魂》、石河的《飞檄集》、李光武的《走过废墟》、秦安江的《洪水》等较有影响的诗作;小说如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董立勃的《白豆》《黑土红土》、邓普的《情满天山》、韩天航的《太阳回落地平线上》、王伶的《天堂河》、王刚的《月亮背面》《英格力士》;报告文学推出了丰收、祝谦、孟丁山等一批名家名作;散文如雷霆的《伊犁趣事》、梁彤瑾的《黑色将军戈壁》《青色乌伦古湖》、赵天益的《情醉旅程》。第四阶段是“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赋予兵团“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三大全新定位,这一时期的兵团文学通过文艺“双优计划”,凸显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等主旋律创作,文艺生产由“高原”迈向“高峰”。《绿洲》《绿风》两本知名文学刊物从形式和内容上改版以提升影响力,“绿洲文艺奖”为推出文艺精品和培养文艺人才队伍搭建了重要平台,丰收的《西长城》、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荣获鲁迅文学奖,14卷本《韩天航文集》和“金戈壁文学丛书”正式出版,为传承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和老兵精神,为推进“文化戍边”与文化润疆工程贡献文艺力量。基于特定的地理位置、文化空间、历史事件及作家身份等因素,兵团文学在题材内容、美学特色和文化意蕴上显现出鲜明的屯垦戍边特色,成为中国西部文学的特殊一支。
一、家国情怀与崇高美学
“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标识,已融入中华文化的灵魂和基因,也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价值引导和情感动力。兵团文学饱含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感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团文学的美学特色。一方面,兵团文学特定的创作主体、题材内容和形象塑造显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共同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兵团文学通过对家国情怀的诗意表述和艺术传达,彰显出一种鲜明的崇高美学。
从创作主体看,兵团文学的早期创作者主要包括部队官兵(转业后的兵团奠基人)、内地支边青年以及因各种原因自流来疆人员。王震、陶峙岳、张仲瀚等兵团奠基人均有气势豪迈、风格刚健的诗歌传世:王震率大军挺进新疆,在翻越险峻的祁连山时写下一首嘹亮战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王震还有几句诗流传甚广,简洁形象地概括了兵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定位,“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该诗被改编为《兵团进行曲》,热情歌颂了部队官兵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转业,“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甘愿在亘古荒原上屯垦戍边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陶峙岳是新疆现代历史上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人物,他挥笔写就的《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意境辽阔、情感激越,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的合作诚意和民族大义表达得淋漓尽致。张仲瀚更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儒将,在文化建设、诗词创作、戏剧排演乃至现代城市规划领域皆有精深造诣,他追求“文以载道”,著有《感怀》《青格达湖》等文学作品,其中《感怀》一诗写道:“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寥寥数语,表达出诗人戍守边陲、埋骨天山的铮铮誓言。同样跟随解放军部队进疆或者有过军旅生涯的创作者还有周非、邓普、伊萍、雷霆、杨树、洋雨、杨眉等。第二类创作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边或自流到新疆,其创作起步较早,但主要是在七八十年代产生较大影响,代表人物包括东虹、章德益、杨牧等。他们或擅长将个体经验与历史命运相结合,书写大历史语境下人物的心理与情感;或礼赞垦荒精神,歌颂改造自然的劳动者形象;或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悲欢离合。20世纪8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诗人以《绿风》《绿洲》和《新疆文学》为阵地,书写西部边地风情,风格雄浑豪迈,颇有盛唐边塞诗之气象,成为“新边塞诗派”的骑手。第三类创作者是在五六十年代因特定政治原因流寓新疆,曾在兵团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因“发愤著书”留下一批风格独特的文艺作品,最典型的代表如艾青,他寓居新疆16年,写下了《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年轻的城》《地窝子》《戈字辈》《铺路》《槐树》《垦荒者之歌》《烧荒》《泉水》《帐篷》《一个老兵》等诗作,或深沉反思历史的苦难与创伤,或热情讴歌荒凉戈壁建新城,风格上交织着苍劲厚重与忧郁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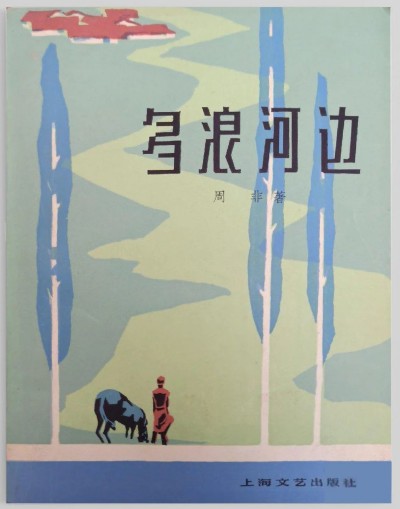
周非《多浪河边》
从题材内容上看,兵团文学始终聚焦新疆屯垦戍边历史,注重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不同历史时期的屯戍状貌,成为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的重要载体。周非的《多浪河边》是兵团早期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以多浪河边的阿英克尔村为叙事场景,尝试以史诗般手法展示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社会变迁。这是一部天山南北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阿不力孜是革命烈士林基路的学生,他身陷囹圄仍然乐观坚强,传抄林基路的《囚徒歌》激励狱友们坚持斗争,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品格引导哈得尔等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这也是一部关于革命者哈得尔的个人成长史。年轻气盛的哈得尔具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他在由“复仇者”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既得益于革命进步人士阿不力孜、买克苏提的启发和引导,也受惠于阿友甫、达吾提等穷苦人家的朴素友谊。这还是一部阿英克尔村的村庄变迁史。小说以鲜明的对比描写表现村庄在经受革命洗礼前后的显著变化,如革命前夕的情景描写,“宁静的多浪河翻起了浪花,各种各样的谣言像臭虫一样,咬噬着每一个人的心”。革命胜利以后,小说转向描写如诗如画的多浪河风光,“多浪河两岸黑色的肥沃的土地上,散发着新翻耕过的泥土的气息。这片被河水哺育着的绿洲,现在才回到劳动人民的怀抱”。
邓普的《军队的女儿》以“军垦第一代”英雄人物、有着“中国保尔”之称的王孟筠为原型素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边题材小说的代表之一。该小说既分享着支边题材小说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又洋溢着革命文艺的积极乐观气息,从而与同时期军垦题材小说“分享艰难”的叙事基调区别开来。主人公刘海英出身革命烈士家庭,父亲是参加过皖南游击战的战斗英雄,母亲坚守革命信仰带着女儿坐牢,小海英在狱中患上了猩红热、中耳炎和严重的关节炎,这段惨烈的牢狱生涯为主人公后来罹患残疾埋下了伏笔。小说开端处,小海英对新疆充满遥远、神秘的想象,受父辈英勇事迹和抗美援朝精神的感染,她立志到茫无涯际的新疆草原开拖拉机。小海英的年龄、身高、体格均不达标,之所以执意瞒着妈妈到新疆参军,一则因为烈士父亲的榜样力量,二则由于耳濡目染二虎伯伯讲述的抗日游击故事,三是主人公幼年时遭遇的牢狱生涯,这段艰苦卓绝的炼狱体验将她从不谙世事的邻家女孩磨砺成“大时代的女儿”,开始自觉思考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
评论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小海英的形象偏于类型化而缺乏典型性,整部小说弥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叙事,如小海英因为年龄未达到参军要求,她与招聘团据理力争,“一个人,要为崇高的目的而活着。”“不参军。哪来的崇高呀?”人物对白与主人公年龄貌似不搭配,“隔”的痕迹较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小说创作于196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交织着梦想、激情与无限可能的年代,一个以“青春”“代沟”为文化关键词的年代,一个后革命濒临之前革命的火花仍然盛开的年代,一个“青春残酷物语”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交相奏响的年代。如果将《军队的女儿》放置在1960年代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细察,就会发现该小说既是一部反映主人公为革命事业不懈拼搏的奋斗史,也是一曲礼赞军垦战士大漠垦荒的劳动颂歌,更是一卷凝结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老军垦集体记忆的生命史诗。从这一意义上说,小海英的革命乐观主义对白及其成长轨迹,深深镌刻上了特定时代的印痕,形塑出一种书写崇高、歌颂崇高的审美品格。
从形象塑造看,兵团文学擅长发掘屯垦戍边精神和胡杨精神的红色基因,大力倡扬现实主义审美原则,彰显一种大气凝重、刚毅坚韧的阳刚之美和崇高之美。这种审美取向在1984年兵团创办《绿风》诗刊时预设的办刊定位中即可看出,“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国当代诗歌为宗旨,以边疆性、青年性、当代性为基本特色”。在兵团文学塑造的人物长廊中,既有对王震、张仲瀚等革命英雄的典型化描写,也有对各民族兵团职工的生动刻画。丰收的报告文学《镇边将军张仲瀚》堪称崇高叙事的典范之作,全书共分为三编,以张仲瀚、王震骨灰魂归天山拉开序幕,先以典型的人物传记叙事手法解释“镇边将军”名字的由来:“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这部报告文学以革命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辅以评论干预介绍新疆屯垦戍边历史,为刻画人物的出场、性格特征及历史贡献奠定基础。首先,创作者有意味地借鉴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如对张仲瀚性格得以塑形的文化空间的多维透视,在描写戏剧文化对张仲瀚童年经历的影响时,文本引用鲁迅先生的《社戏》并加以评论干预,“在农耕文明统领中国的漫漫岁月里,无论出身官宦人家还是农桑布丁,‘戏文’于一个人的发蒙是不可忽视的”。其次,文本叙事将广角镜头移向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滚滚洪流,爬梳苏俄文学、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张仲瀚成长经历的重要影响。再次,文本擅长运用旁观者的见证视角,表现张仲瀚对新疆地理风物和近代历史风云的熟悉,歌颂其文韬武略的英雄气概与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老部下谢高忠的见证人视角被多次运用,比如对张仲瀚高尚情操的评价,“我们这一辈人中,没有谁比他更相信理想的力量。没有谁能比他把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最后,文本旁征博引,广泛征引各种文献史料及回忆录,以具体入微的细节描写烘托人物性格。如文本在表现张仲瀚的深厚家国情怀时,引述了张仲瀚本人撰写的回忆录《忆新疆》,介绍其在部队挺进新疆之前,面临多种人生选择却矢志不渝毅然进疆的壮举。此外,文本以起义部队官员罗汝正遗孀李秀芹的纪念文字《海样的胸怀》为例证,描写张仲瀚不拘一格爱惜人才的广阔胸怀。
在兵团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谱系中,既有王震、张仲瀚、陶峙岳等将帅人物,他们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还有千千万万个宛如螺丝钉一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兵团职工,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崇高,正如散文报告文学集《天山之子》的序言“赤子的歌”所论:“历史,要由开发者去写,新疆的历史,正在由新疆各族人民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书写。”如傅志华的《天山探路》热情赞美了勘探人员在天山冰峰与哈萨克牧民之间的深厚情谊。筑路工人历尽艰险修建了一条越过天格尔冰峰、贯通南北疆的天路,为了顺利修筑公路,雪山之上哈萨克牧民阿里登奶奶把仅剩的半袋面粉送给勘探人员,“我的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我浑身上下感到雪地里遇着篝火般温暖,我觉得手上接到的不是半袋白面,而是一颗热情的心”。
丰收的《绿太阳》被誉为“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这是一部反映兵团军垦战士戍守西部荒原,克服艰难险阻垦荒修渠的报告文学,叙述者以放眼古今的宏大视野勾勒西域和中原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为塑造兵团垦荒者形象提供了宏大纵深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叙述者以自身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文本叙事,借助鲜活细腻的事件描述和人物刻画,塑造出一组组具有典型性格特征的“奉献者/牺牲者”形象。对于开垦吾瓦盐碱地的军垦战士来说,吾瓦荒地就是他们挚爱的对象,“一切都是公正的,付出一分情就能得到十分爱。苍凉遒劲广袤的深层蕴藏着柔情万种”。宋献银就是垦荒英雄群像中的一员,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战斗英雄快速适应身份转变,扛起铁锹和坎土曼与盐碱地争夺生存空间,昔日荒芜萧条的盐碱地上种出了香甜的库尔勒香梨,为南疆梨城增添了新的传奇。
值得关注的是,兵团军垦战士以“人定胜天”之豪迈气概积极改造自然,但又自觉拒绝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他们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如侯晋标在历史的逆流中用生命保护白杨林,为戈壁滩守护一丝绿色。无论生存环境多么恶劣,军垦战士始终高扬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或发挥生存智慧就地取材,从极端环境中发掘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品”,如从盐碱土里分离出做菜用的食盐,从胡杨树刮“胡杨碱”蒸馍馍;或在辛劳困顿与诸多挫折中保留一份浪漫心态和审美追求,“每年五月,红柳开花,母亲把红柳枝插在洗干净的玻璃瓶里,窗台上摆一瓶,装衣物的‘墙’上放一瓶……后来,母亲种的沙枣树开花了,瓶里的红柳枝就换上了一束束沙枣花”。李希贤从西北工学院毕业后远赴新疆筑堤坝修水利,他甘愿坚守基层,即便亲历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风浪,依旧以一种“浪漫心态”应对挫折磨难,用生命诠释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情怀,他怀着对水利工程的深厚感情,古稀之年仍居住在博斯腾湖引水工程工地,“屋顶依然浪漫地闪烁着星光。风沙依然浪漫地进进出出。蓝月亮依然浪漫地流进棚屋和他挤在一起”。这种“浪漫的崇高”已经镌刻进兵团人的血液和灵魂之中,成为兵团精神的重要底色。
“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它对混合了妩媚与恐惧、高度与深度的‘崇高’的追求远甚于对优美或古典美的欣赏。”学界既有研究注重凸显兵团军垦战士以奉献和牺牲为内核的崇高美,本文则倾向于使用“浪漫的崇高”来描绘这个西部特殊群落的精神生态和审美品格:他们身处偏远西部,远离繁华都市,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垦荒建城,住地窝子、啃窝窝头,即便如此,仍然以非凡毅力超越极端生境的限度,展现个体的能动性。应当说,兵团文学具有以奉献精神和利他主义为伦理特征的崇高美,这种品质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传承了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丰富内涵,表现为个体在历史的洪流中甘愿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就民族大义,个体能够将人生目标与奋斗理想整合到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大叙事之中。这种崇高美不仅体现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或历史转折期的风浪之中,也融入了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如韩天航、施祥生、王伶、钱明辉的小说,赵天益、梁彤瑾的散文,李光武、秦安江、郁笛、贺海涛、彭惊宇的诗歌。
兵团文学“浪漫的崇高”美学品格在表征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纯粹美。正如评论家对“金戈壁文学丛书”的评价:“没有杂质杂音,没有地沟油的污染痕迹”,“像鹰一样栖息与翱翔,像钻头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大地上钻探,专心致志、义无反顾”。丰收的《西长城》全景式再现兵团60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塑造出“沙海老兵”刘来宝、苏联援华专家迪托夫、进疆女兵肖叶群等典型人物,热情歌颂兵团人屯垦戍边、淡薄功利的博大胸怀和诗意气质。二是体现出鲜明的融合之美。从历史的纵轴上看,兵团文学融汇了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从共时的维度出发,兵团文学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军旅文化与群众文化、人与自然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在诸种文化元素交流、碰撞与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审美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从美学特质上看,兵团文学萃聚了西部边地奇谲险峻的自然风光之美、丰厚凝重的人文历史之美、悲壮激昂的兵团人风骨之美。
二、身份认同与乡愁美学
家园意识与乡愁情结是中国文学的恒定母题,它紧密牵系着乡土社会的情感结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种叙事母题和审美体验也是兵团文学的显著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兵团在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层面都成为被高度显影的存在,一则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劳武结合”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二则因政治风波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兵团虽偏居西北一隅却在特定时期成为“避风港”,接纳了大量从全国各地涌入的自流来疆人员。作为主客观交互作用的产物,兵团文学的美学特征既受制于历史文化情境,也和创作者的期待视野、接受心境和审美感知息息相关。
兵团初创期的人口构成以就地转业的部队官兵和内地省市从各种渠道迁移来疆人员为主,这一时期兵团文学创作者经历了生活空间的转移和“人地关系”的重构。他们眼中所观察到的边地风物与屯垦戍边人文风情,或聚焦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的发展现状,或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及近代旅新人士的新疆书写所形塑的“前理解”影响,或因创作者囿于政治风波导致审美感知偏移,这种交织着时代悲剧与个体创伤的复杂情绪影响到文学书写的情感表达。
杨牧被誉为新边塞诗“三剑客”之一,从1964年西去新疆到1990年南归,他在兵团度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26载光阴。杨牧对新疆的书写,经历了从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切换,其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天狼星下》表现得尤为突出。该书采取流浪汉小说叙事模式,以第一人称回忆视角描绘了一部西部“盲流”的心灵史。在叙述人眼中,边地风景显得荒凉孤寂、了无生机,“宽阔的戈壁像一张脱光了毛的驴皮,一望无际,直铺到天地的衔接处。无一根草,无一棵树,无任何可以叫人联想到生命的东西”。对叙述人而言,新疆不仅自然风光与其“故乡”成都平原的葱郁富庶有着迥异之别,人文风情亦是如此。叙述人因走投无路到兵团投奔“朋友的朋友”,初来乍到就经历了妖魔山被骗、从安集海去乌苏的途中被司机抛弃,这种流寓异乡的绝地生境愈加凸显叙述人的流浪者心态,家园意识显得遥远而缥缈,对故土的“恋地情结”挥之不去。叙述人被赋予一种无所依托、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位置,满眼所及皆是荒芜的戈壁滩和尔虞我诈的人群。“我本来在东,命运偏要叫我向西;我向西了,车又全是向东去的。”这里叙述人秉持的是局外人视角,在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凸显内地人身份,对新疆带有刻板的边地想象。“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文本中的风景叙事,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创作者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塑过程。随着来疆时间的推移和美好人性的融入,叙述人眼中的风景及人地关系逐渐变得充满温情,这些美好人性如电影蒙太奇镜头闪现在叙述者流寓新疆的不同时刻:初到新疆时姜大哥多番关照,进疆火车上邂逅的同路人何纯芳,共同历险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苏珺瑜,逆境中吐拉洪老人的善意保护,文学创作道路上艾青等前辈作家的引路……叙述人逐渐对兵团产生了深挚的情感投射和身份认同,由川娃子转变为“南疆乡村的伊敏江”。
杨牧的《天狼星下》带有浓厚的反思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某种意义上保留了些许“伤痕情调”:“我无法忘记。那是一种残酷的声音,断头的声音。一如我无法忘记我用小提琴、书籍和二十岁就拥有的浑身伤痕和弃釜沉舟作为赌注所兑换来的神奇、荒诞、贫瘠、富有和永远不再结痂的残缺!”但《天狼星下》显然超越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苦难叙事,它尝试摆脱对个体苦难的感喟哀叹,自觉引入时代和民族文化的多维坐标,反思极端环境下人性的世情百态,旨在穿透政治历史文化的重重雾障,探询悲剧人生的历史动因。
如果说,这段西部流浪经历为杨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那么,随着作家不断适应并扎根新疆兵团屯垦戍边事业,这种边地体验促成了作家情感结构与审美心理的迁移。1981年,杨牧发表《我是青年》并震撼诗坛,引发一代读者的深切共鸣,也奠定了杨牧的西部文学旗手地位。20世纪80年代,杨牧出任《绿风》诗刊主编,倡导具有西部地域特色、风格悲壮激越的现实主义创作美学,以《绿风》为阵地推出一批诗人,戈壁明珠石河子也被文坛誉为“诗城”。如果将杨牧在疆期间的创作构建起一组文本序列,就会发现《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大西北,是雄性的》《汗血马》《鹰》《色力布亚》和长诗《边魂》以炽热的情感讴歌了西部山川风物,展示了兵团军垦战士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杨牧身体力行的推动下,这批以西部自然风光和拓荒者人生命运为表现对象的诗人群体被命名为“新边塞诗派”,与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盛唐边塞诗遥相呼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中的西部景片。从四川流浪到新疆,诗人杨牧经历了由“盲流”到兵团职工的身份转变,其叙述视角与创作心态也表现出由“旁观者/流浪者”到“局内人/主人翁”的转变。这种对新疆兵团的身份认同形塑了杨牧文学创作的美学特质:融悲壮之美于苍茫孤寂的戈壁大漠,寓人性温情之美于兵团人的生产劳动与心灵世界。通过在文本中反复运用红柳、胡杨、梭梭、天山冰峰、盐碱地、伊犁马等极富新疆地理标识度的文学意象,杨牧一方面推动了兵团文学审美符号系统的构筑,另一方面完成了由流浪者想象“他乡”到亲历者为“家乡”抒怀的华丽转身。
兵团散文作家梁彤瑾是资深新闻工作者,1960年代末赴新疆插队,从此与新疆结下了深厚情缘,其散文作品以新疆屯垦戍边史为内在逻辑线索,赞美新疆奇特瑰丽的自然风光与斑斓多姿的人文风情,尤其是《黑色将军戈壁》《紫色博格达峰》《青色乌伦古湖》《红色玛纳斯河》系列,以陌生化手法渲染新疆之大美,如对天山博格达峰的钟情,“看那天池水,此刻也是姹紫嫣红,或者说是紫中带蓝,黑中泛紫,风吹起的涟漪都是紫洇洇的,把周围的森林也染成紫色的人”。巍峨苍劲的博格达峰,葱郁挺拔的雪岭云杉,绚丽的云彩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天池水中,作者有意避开审美惯性,采用“紫”“蓝”“黑”等颜色词汇,通过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意境营造,构建出一种独具匠心的色彩美学。在《青色乌伦古湖》中,作者既描写了乌伦古湖清丽秀美的自然风景,也表达了对生态环境遭遇破坏的忧思。《红色玛纳斯河》携带着丰富的文化意蕴,“红色”是一种革命书写,一种对新疆当代屯垦戍边历史的符号表征,既指向战火硝烟中解放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也指向兵团成立之初垦荒战士付出的血汗,还指向兵团第二代诞生的脐血,象征着希望与未来。梁彤瑾散文的魅力,在于他倾注全部情感,将一种浓烈的“乡愁”融入对新疆这片土地的审美观照。
王伶的《化剑》聚焦新疆和平解放之初的风云激荡岁月,解放军部队官兵巧妙化解矛盾,成功实现对起义部队的改编,刘铁与俞天白这对昔日战场上的死敌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建立了生死情谊,小说中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垦荒战士从内心深处将兵团认同为“家乡”,对白手起家的兵团农场充满无限眷恋。在巴格其农场的垦荒战士眼中,棉花是一种极富浪漫情调的植物,“原野上还有另一种颜色令人着迷,那就是白色——白色的棉花地,白色的棉山,白色的拾花姑娘”。地窝子则被形象表述为“地下宫殿”,与延安黄土坡上的窑洞相类比,“在这儿,有这么大片的地,何不造些地下宫殿——把地挖个三两米深,七八米见方,上面搭些胡杨树枝和红柳芦苇,不就成了吗!”
韩天航是上海支边青年,也是新时代兵团重点推出的作家代表,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出版了《回沪记》《母亲和我们》《我的大爹》《太阳回落地平线上》《夜色中的月光》等屯垦戍边题材小说。此类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上海支边青年,他们经历了“下乡”与“返城”,面临着生存空间的转移,文本采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反映支边青年回城后成为被拒弃的“多余人”,亲情在历史的洪流中遭遇扭曲,“乡关何处”的漂泊感四处弥漫。《棚户记事》中,主人公阿祥回城后遭遇兄弟反目,居无定所,关键时刻曾在新疆兵团一起支边的阿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走向新的生活,“有人说,兄弟是无法选择的,但朋友却可以选择,所以可以选择的朋友要比无法选择的兄弟还要亲”。阿祥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寻找另一种人生,从股市中尝到甜头并摇身一变为“股市阿祥”,日渐迷失在光怪陆离的商业大潮之中,最终重返新疆达成赎罪与和解,新疆成为承载理想信念的心灵家园。《养父》中的“沙驼”为了履行诺言收养了上海支边青年田美娜的私生女,宁愿自己一辈子不结婚,含辛茹苦也要将养女抚养成人,后来又帮助养女回到上海寻亲并站稳脚跟,“沙驼”是小说叙事的情感黏合剂,当文本中所有的情感裂痕被缝合时,他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兵团农场,成为胸怀坦荡和高尚情操的代言人。如果将韩天航的“兵团题材小说”与“上海滩系列小说”展开文本对读,就会发现他扮演着文学“摆渡人”的角色:对于曾经挥洒过青春热血的兵团,他饱含情感描绘那里的一沙一砾、一草一木,塑造出杨自胜(《我的大爹》)、刘月季(《母亲和我们》)、林凡清(《牧歌》)等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典型人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歌者。相比之下,上海作为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代名词,成为灵与肉苦苦挣扎的场域,也是展示兵团人性崇高美的侧影和衬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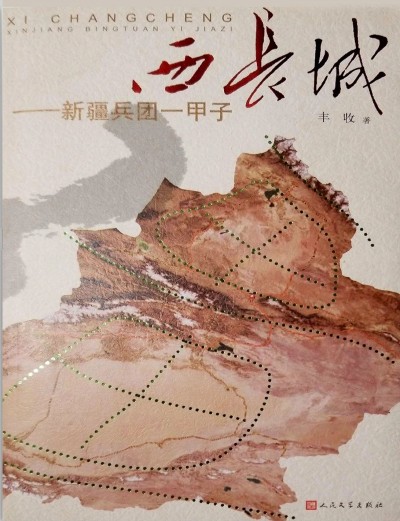
丰收《西长城》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兵团文学高扬主旋律旗帜,推出了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学力作,为讲好兵团故事、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文艺力量。2014年,丰收推出史诗般纪实文学《西长城》,旨在为兵团一甲子树碑立传,该书以“古道天涯”启幕,包括“屯垦天山下”“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长城”“年轻的城”六卷,最后以“乡关何处”收尾。《西长城》以作者数十年辗转天山南北采集的兵团“老军垦”口述史为素材,采取恢弘的篇章结构记录几代兵团人的艰辛创业历程,通过生动细腻的人物形象塑造,绘制出一幅别样的乡愁美学图景。兵团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书写,从周非的《多浪河边》到许特生的《帕里黛与帕里夏》,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种凸显文化融合的文本呈现极富叙事张力:兵团是凝聚各民族的大熔炉,各民族之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成为推进新时代屯垦戍边事业向纵深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情感催化剂。在《西长城》中,维吾尔族老人马木提视树如命,却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为了十八团渠通水甘愿放弃自家宅院,“一家人悄然离开老宅院时,马木提和老伴恋恋不舍走在最后。老伴抱住一棵香梨树流眼泪了。真是舍不下这些亲手栽种的树呀!”在车排子垦区,教导员杨新三和铁木拉洪的生死情谊,谱写了一曲跨越时空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兵团文学的乡愁美学以流动性和融合性为典型特征,一方面,创作者身份的多元性及跨地域流动,推动兵团文学创作对“家乡”的指认由“出生之地”转向“成长之地”,情感上杂糅了童年记忆与兵团体验,这种“流动的乡愁”恰恰是兵团人对屯垦戍边事业高度认同的审美折射;另一方面,兵团的“大熔炉”特性使得兵团文学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和审美共用空间,文本中构筑的乡愁景观地图,成为新时代“石榴籽”文化意象的情感表达。
三、结语
立足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主线,也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艺批评话语创新的重要遵循,它要求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砥砺深耕、笃行致远,为各民族间构建起一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路径、教育路径、文化路径和审美路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守护着漫长的边境线,地缘政治位置极其特殊,一方面延续了古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凸显近现代以来新疆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创新。从这一意义上说,兵团文学呈现出的“浪漫的崇高”美学,呼应了秦汉以来西域与中原之间日益深入的互动交流,以文学为载体书写“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浓厚家国情怀,建立起一种“以大我之心”勇担历史使命的共同体美学。此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特殊组织,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较为频繁,各民族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种彰显主体间性的空间构型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审美主体的情感结构,他们通过“故乡”与“家乡”的叙事迁移和情感转换,既保持“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美”,进而达到“美美与共”的叙事目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审美路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是新疆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地貌中的独特存在,这份独具特色的审美品格与精神气质,既缘于新疆萃聚多民族、多文化及奇谲瑰丽自然风光的客观条件,也基于兵团集党政军企职能于一体的特殊建制,构筑起以西部自然风光和几代兵团人人生命运故事为表现对象,风格遒劲悲壮,充满慷慨豪迈之气,凸显屯垦戍边文化特色、传递兵团声音、装点兵团色彩、散发兵团味道的文学审美景观;也为身处消费文化和全球化浪潮之中的我们,在坚守崇高美学、寻找乡愁记忆的同时,尝试以兵团为方法,全面梳理总结兵团文学的审美经验,进而形塑共同体审美与叙事,最终由地方经验走向广阔世界,打开了一扇文艺的窗口。
*本文系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邹赞 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7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