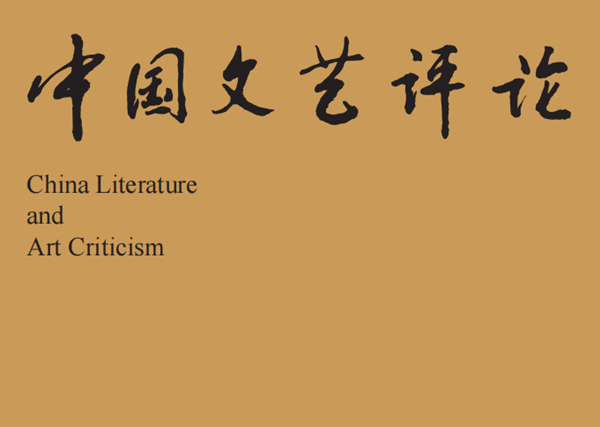
【内容摘要】 冯契先生基于鲁迅的“金刚怒目”说,进一步将此深化为中国美学思想两大传统之一,并认为这一传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故而其相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羚羊挂角”审美传统更重要。“金刚怒目”式的审美关注现实的人格,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实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并提出了新时期具体的人格培养方向,即自由的平民化人格。这在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涵摄与吸收,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独特品格。
【关 键 词】 冯契 美学 金刚怒目 马克思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蔚然大观。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方法也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笔重要的遗产。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受众最多,影响最大。诸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展开了讨论,并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参照。然而,在梳理这段历史时,诸多学人对冯契的美学思想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不仅使得我们对20世纪下半叶美学发展的认知存在盲点,还使得冯契美学的当代意义被忽略。事实上,在当代美学发展的路向,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立足中国立场,紧扣中国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和美学史话语体系”这一议题上,冯契已著先鞭。

青年冯契(来源:“纪实人文频道”微信公号)
冯契的“智慧说”体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闳深广大,特色鲜明。在美学思想上,先生的一大贡献便是发掘出了“金刚怒目”的审美内涵,并将之上升为中国美学最重要的审美传统。可以说,冯所重视的“金刚怒目”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美学融合汇通的精彩展示,也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汲取传统美学思想的可能性、为当代美学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一、“金刚怒目”的提出:从鲁迅到冯契
“金刚怒目”作为一种审美范型由鲁迅在论述陶潜时提出,其言:“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在这里,鲁迅批评“论客”们过于强调陶渊明“飘飘然”而忽视了其“金刚怒目”的一面。因此,论客们描述的并非是真实的“全人”。可见,“金刚怒目”是构成人的真实性的必要环节,也是整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相关,其又言道:“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通过批评过度拔高人的某一层面,进而拔高该人这一评价方式,鲁迅强调的是人之常情、常人之情。由此进一步言,“金刚怒目”在鲁迅这里被用来指向具有喜怒哀乐情感的常人,而不是君子或圣人,或某方面突出的人。君子、圣人只是少数人,关于他们人格的描述,其实只能指向少数人,甚而或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常人则不同,常人就是在现实中的一般人,具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因而更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这样来看,鲁迅借由“金刚怒目”强调的“全人”,是现实人格的整全。但从上述“‘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等引文看,鲁迅并没有认为“金刚怒目”或者比“飘飘然”在意义层面更重要。“金刚怒目”虽然因为被人们所忽视而在此被单独强调,但就人格本身的整全性而言,二者相对而生,同样是人要具有现实的真实的整全人格的应有之义。
冯契注意到了鲁迅对于“金刚怒目”式的重视,并自觉接受了鲁迅的看法。这种接受背后体现了二者皆关注人的现实性和整全人格。但冯先生并不止步于要求关注现实人格,而对此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哲理提升和深化。
首先,冯契用“金刚怒目”与“羚羊挂角”这个对子替换了鲁迅所讲的“金刚怒目”与“飘飘然”。“羚羊挂角”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出现在严羽《沧浪诗话》中。严羽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可以看出,其本色用法描述的是基于诗人审美感性而来的诗境超脱通透,不可指摘。因此,冯先生的这种替代实现的是从对人格的分析、评介到审美风格的视角切换。同时,鉴于“羚羊挂角”说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把“金刚怒目”与之比对,则“金刚怒目”的理论适用域也自然扩大了。同时,又因为在冯先生这里,“金刚怒目”关注现实的人格,所以,“羚羊挂角”就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审美风格或是意境的营造,而是和人格关联了起来。这种关联就使其摆脱了单纯作为一种风格的描述,而上升为一种立足于人格的审美范型。结合其本色审美话语,这种范型所昭示的是人自我心灵境界的升华,而“无迹可求”等说明了此种心灵升华是通过对现实的诸多因素或“迹”的超越而实现的。所以,这种审美范型把人格引向的是对现实的超脱。简言之,出于对现实人格的考量,冯先生将“金刚怒目”与“羚羊挂角”理解为中国美学传统的两大范式。
但是,在冯契看来,“金刚怒目”的传统其实却比“羚羊挂角”的传统更重要。因为“羚羊挂角”把人引向超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是对真实现实问题的规避或回避。但“金刚怒目”不同,它指向的是人格在现实中的展现,并没有超脱之意。“怒目”是一种主体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金刚怒目”则表明在这种“怒目”式的不满情绪中,不掺杂利害关系,纯粹是主体对于现实的关切。那么这种对于现实关切的人格为何更重要呢?这实际上是由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决定的。“在实践与感性直观中,人能获得客观存在感。”感性直观的运动、客观存在感的获得需要在现实实践中进行。而这种实践即劳动,先生认为“自由劳动,是劳动与意识、感性活动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的统一,这就是人的类本质”。也就是说,现实人格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其与我们作为人的类本质相关。我们进行现实劳动,在劳动中形成人格。基于此,“金刚怒目”传统的意义便远高于“羚羊挂角”传统。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先生拈出了“自由劳动”一说。冯先生认为,“人类在本质上要求自由,要求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要求自由是人类的本质要求,自然也是在劳动中实现的。但与一般对于劳动的强调不同,先生强调“自由劳动”注意到了在劳动中人的境界的提升,而这种境界与审美有关,也就是说追求美也是自由劳动的应有之义。审美在人的本质这一层面上,关联着“自由劳动”,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植根于自由劳动。由此看来,“金刚怒目”对于现实人格的关注,也关系着现实人的自由。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视域内,从现实的人的本质出发,冯契对于鲁迅“金刚怒目”说进行了转换。这种转换,使得鲁迅先生的提法更具有了理论意义。

冯契《怎样认识世界》
二、“金刚怒目”作为审美传统的历史谱系
冯契言:“哲学家的新境界既然是从哲学史总结出来的,是哲学史论争的辩证的综合,那么,哲学史的辨证发展过程也就成了哲学家的新学说、新境界的论证。”无疑,冯契的研究也具有如此特色。具体到“金刚怒目”说上来讲,从先生的论述来看,其认为“金刚怒目”传统渊源有自,且随着历史的演化,其所呈现的审美形态也不断地丰富起来。而这种丰富形态的背后有着一种逻辑的演进,呈现出了它的基本审美意涵。
冯契对此的论述,散落在其关于“艺术意境”与“典型性格”的论述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于每个时期都拈出一些重要的表述,并且认为他们先后有逻辑上的衔接。这种衔接不是无发展的重复,而是与其他审美论题相对照,以彰显出意义内容得到了拓深,从而形成了这种传统。冯契从先秦的“诗言志”开始,认为“讲‘言志’离不开情和志,就是吟咏情性和抒写怀抱,感情和志向这两个方面。首先,讲怀抱就离不开政治和教化,离不开社会作用,这就要抒发对现实的美刺,或如孔子所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肯定了儒家具有美刺比兴特点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意义,并进而认为六朝人提出的“兴寄”说也属于这一类。相应地,“风骨”同样是六朝时期一个重要的审美观点,先生认为“艺术作品中的‘气’就是‘风骨’”。那么“气”又有什么含义呢?这要追溯到先生对孟子“志气”说的解释,“照传统的说法,情志首先表现于‘气’,如孟子讲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紧跟着‘志’,‘气’指人的勇气、气魄、气势,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状态,‘浩然之气’即大无畏精神。后来人们讲文气,是指作品的气势”。也就是说,在冯契看来,艺术作品的“风骨”根源于艺术家本身之“气”。这种人之“气”是道德的精神状态,落实到作品中则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我们再看先生另一段论述:“六朝人讲抒情艺术理论,最主要的是情志表现为气势、气韵,要求艺术作品有‘风骨’;同时提出艺术要为人生,提出‘兴寄’。‘风骨’和‘兴寄’是当时艺术意境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在这里,“风骨”和“兴寄”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不同层面,“风骨”是就作品而言,“兴寄”是就作者而言。而且,基于“情志表现为气势、气韵”这一前提,二者又是内在地连接在一起的。而“风骨”说的审美价值,又在后来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反思中得到彰显,并泽及后世。冯契言:“真正盛唐的传统,要求艺术具有风骨、兴寄,讲艺术是为人生的。这个传统在唐人那里演变到后来,就成为白居易、韩愈的理论,白居易说‘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了诗的美刺比兴的作用;韩愈讲‘不平则鸣’,因为这时社会矛盾加深了,他们就强调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矛盾,有批判现实的作用。后来的大作家都强调这个传统,认为诗文要干预现实,反映社会矛盾。一直到黄宗羲讲‘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强调风雷之文,鲁迅强调‘金刚怒目’,都是这个传统。”到此,“金刚怒目”传统的审美形态的历史脉络得以完成,绳绳相续。而“言志”“风骨”“兴寄”“金刚怒目”等,这些审美议题则体现了这种历史演进的逻辑,也彰显了不断丰富的审美意涵,即始于儒家诗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持续保持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冯契看来,“金刚怒目”传统自古以来在理论上都要求着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而不单单是追求艺术的自律。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内在要求。在20世纪百年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致主张艺术要超越本身形式的“自律”而“介入”社会生活。冯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将之溯源到先秦儒家,通过对历代相关审美概念,如“志气”“风骨”“兴寄”等的深究,构建了一条“金刚怒目”传统的发展脉络。这样的传统构建,既符合美学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又有着鲜明的理论指向。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指导下,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精彩书写。冯契力图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合。
在这种历史梳理中,“金刚怒目”主要涉及主体在艺术活动中的倾向。换句话说,“金刚怒目”作为审美范式主要是针对艺术活动而言的。而艺术活动主要涉及价值评介的问题,因此,为了明白“金刚怒目”的审美内涵,这里还应该进一步追溯到先生关于价值的论述。先生言:“价值界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凭着对自然物进行加工而造成的文化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审美作为一种价值,也是人化的自然,对自然的加工的结果。艺术创造也是人类自身现实创造的一部分。同时,对于自然的加工并不是个体独自完成的活动,人化的自然既然是在社会历史中发展形成,那么其必然就与社会组织密切关联。因而,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活动也是在社会生活中完成的。这就从艺术活动的实际发生上说明了艺术介入社会生活的必然性。这种介入,经由创造主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艺术创造根源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者自身,因此它是作者本身含有的道德等情志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创造主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赋予了艺术创造所要传达的社会面貌。就“金刚怒目”而言,现实社会的不平、障碍进一步地激发了主体克服它的意志与愿望,而这些意志和愿望在艺术家身上所激发的创作冲动,将之凝结为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性格。同时,对于鉴赏者而言,也是通过对典型人物、性格的欣赏,与之相较,使得自己的情志得以陶冶,人格得到了提升。
通过“金刚怒目”式的审美活动,人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涵摄,从现实情感出发升华为一种人格的崇高。借此,这种审美传统的意涵实际上可以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崇高”相比较,吉尔伯特和库恩在评论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时说:“在这一著作中,他似乎要把诗人和演说家的注意力从文学的表面形式召回到内在的意义上去。”与之相较,“金刚怒目”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突出的也是艺术品的内在意义,即表现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培养自由人格。但是与西方传统美学的“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就理论底色而言,“金刚怒目”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实现在本质上与社会实际生活相关联。社会生活是其所要彰显的内在意义,而不仅仅是主体内在情绪的表达,或者感官的愉悦。再者,西方传统中的崇高,并不构成追求艺术形式自律的审美判断的对立面。而在冯契这里则存在着这种对立。“羚羊挂角”传统对于现实的“迹”的超脱,强调的是主体艺术活动的自足性,更多的需要关注艺术自身;而“金刚怒目”作为一种传统的拈出,如前所述,则与追求形式自律的“羚羊挂角”相对而存在。

冯契《冯契文集》
三、“金刚怒目”的审美特质
“金刚怒目”的话语谱系蕴含着理论意涵。冯契这种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梳理,也有着理论动机,即其探索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能回应美学史上的一般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从美学基本议题的视域来看,便可以看出“金刚怒目”说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美学内蕴。这种美学内蕴典型地体现在关于真善美三者关系以及理想人格的指向这两个议题上。在前者中,冯先生特别强调了审美的意义;在后者里,先生强调了审美所造就的人格的普遍性。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自美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近代成立以来,审美就自觉地与真、善区别开来。关于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聚讼纷纭。冯契自然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先生的“金刚怒目”说主张真善美三者应该在现实人生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冯契认为理想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起点与沟通二者的桥梁。而审美理想又是其重要方面,它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形象化的理想”,“不是抽象概念,也不同于规则和规范,而是体现于生动的形象,渗透了人的感情”。可见,审美本身就是我们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又因为其指向的是生动形象以及人的具体感情,所以在我们参与现实生活世界中审美具有独特的意义。结合上面所述,先生这里所言的审美,无疑便是“金刚怒目”式的审美,关注社会现实,为人生而艺术。这种审美与作为参与世界的其他方式的真和善是统一的,三者统一于“理想化为现实的精神自由”。
具体说来,“真”就是全面的认识。冯契认为这种全面的认识,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认知活动,而是“符合人们利益、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金刚怒目”与此重认识的关联就在于,“金刚怒目”式的审美在现实生活中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先生言“就艺术的真实性来说,艺术理想有两个方面的物质前提:一个方面,艺术理想的源泉是社会生活以及人本身;另一个方面,艺术理想要成为现实,一定要取得物质外壳,一定要有物质媒介来把它表现出来。……从内容方面来看,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要求有真实性,艺术理想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如果没有真实性,那就没有艺术”。艺术植根于真实的生活。任何艺术创造都需要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素材与内容,都是对生活的认识。再者,艺术作为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认知方式要使得生活的逻辑体现出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在这里,艺术真实性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的真理性认识。但是与单纯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认识相比,“金刚怒目”式的审美作为参与社会的方式还有两重意义。一则,艺术不仅能反映生活,还能看到发展的趋势。“艺术理想不等于生活中现成的东西,艺术家凭借理性的直觉,抓住了现实生活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并加以典型化、理想化,这样,艺术可以使人看到生活的本质,看到它的发展趋势。”与单纯的认识关注现成的社会现实物不同,艺术家凭借理性的直觉能捕捉到生活中可能性的存在,并将之呈现出来。二则,因为这种呈现是通过典型化、理想化的形象创造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在其中呈现出的生活本质和发展趋势能够被人,而且是更多数的人,直接感知。也就是说,“金刚怒目”式审美所呈现的真理性认识在接受上更具有普遍性。这种对于全面认识及其被接受的普遍性的强调,无疑得益于冯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于此重立场,先生认同唐人对“彩丽竞繁”的六朝文学的批评。六朝文学的问题在于其过于注重艺术形式的自律,而忽视了对于真实生活的反应,故而批评其“兴寄都绝”是成立的。只是先生比唐人更进一步,认为在“兴寄”背后还应呈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善”主要是通过道德评价来进行的。首先,冯契认为“道德理想与艺术理想的结合,是优秀艺术作品的内在要求”。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介,并不能满足于艺术自身的角度,也需要对作品进行道德上的评价。这种要求是对艺术反映生活真实性的深化。现实生活并不仅仅是由人的一系列行为事件组成的,也包含着对于主体行为的评价,而最主要的是对于人的道德评价。故对于艺术真实性而言,在揭示生活真实性的同时,也彰显出了蕴藏在真实性中的道德意味。“无论是塑造性格还是创造典型,都需要有一种道德理想,如果缺乏先进的道德理想,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体现人道原则,那么这样的艺术总是无力的,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里,先生进一步将道德评价凝练成三个维度:先进的道德理想、爱国主义、人道原则。道德理想涉及的是主体主观意志层面,爱国主义关注的是道德中的文化或民族性因素,人道原则代表的是主体作为人的普遍价值。可见,先生主张美善相通,不单单看到二者在理论形式上的关联,更看重的是在这种关联背后,道德赋予审美的具体意义维度。“金刚怒目”式的审美经由道德评价展现出来,其关注的是在普遍人性、文化背景、个体能力三重视域中的现实之人。再者,审美具有的移情机制使得美与善、自然与社会相通。“品德、道德境界与现实的社会伦理、社会的道德秩序是统一的,不仅是社会秩序,而且与社会相联系的自然界,也因为人的活动,当然也有移情的作用,而具有道德色彩。这种道德色彩,又往往与艺术的境界相联系着。”个人的德性与社会道德秩序相统一,但是要与自然界相联系,就必须通过移情的作用。“金刚怒目”因为其本身关注人的德性,故而更强调移情对于道德的落实的作用。通过移情,“情景交融,物我同一”,人与社会、自然的对立被打破。我的情感可以灌注到自然界,使得自然事物呈现出情感色彩。此外,“金刚怒目”式审美在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移情作用发生的主体不是静观的自我,而是在活动中的自我。移情活动的进行不是神秘的、偶然性的,而是发生在人的现实活动中的,具体来说,就是发生在主体人化自然的自由劳动中的。
关于真善美三者关系,冯契认为,“美是以真和善为前提,美和真与善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如上所述,审美在真理性认识、道德评价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意义。这就表明,美以真和善为前提,并不意味着其在重要性上逊于二者。与之相应,先生通过对于荀子所提出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分析指出,“‘全’是指全面的认识,‘粹’是指纯粹的品德,‘全’和‘粹’是真和善,再加上礼乐的培养,就成为美。”单纯的真和善是不够的,只有再加主动的礼乐陶冶,才能成为美。这就说明,审美不仅与真、善相关联,实际上还标记着认识和道德更高层次的状态。
(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指向
如前文所言,“金刚怒目”关注的是现实人的整全人格。实际上,冯契对于“金刚怒目”的人格指向,有着更具体的看法,即指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也就是说,“金刚怒目”关注的是现实中平民大众的精神自由。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近代人对培养新人的要求,与古代人要使人成为圣贤、成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
在人生理想方面,近代哲学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提出了“新人”的理想,就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想。鲁迅对真实的自由人格的精神面貌作了很好的描绘,说这样的人格既自尊,又尊重别人;既为了大众的利益进行韧性的战斗,又完全清除了寇盗心和奴才气。
平民化的人格,首先意味着实现这种人格的是平民,一般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之。相比之下,“羚羊挂角”传统注重艺术的自律、对于现实的超越,这无疑只对于少数人才有可能。因而,“金刚怒目”的人格指向就具有了更加普遍化的特征。
从引文看,这一说法也是得益于鲁迅对于自由人格的描绘,与前文所言其“金刚怒目”说也源于鲁迅若合符节。这一方面可见冯契受鲁迅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金刚怒目”说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说在理论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此种人格对于主体而言,一则是要求主体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要尊重。别人是相对于我而存在的个体,那么对于别人的尊重,实际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我与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又因为主体自身也是平民中的一个,那么这种对别人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这样,尊重别人与尊重自己便内在地联系了起来。再则,别人在这里,还是一个群体性概念——大众。自我本身就是平民大众中的一员,主体应该为大众去获取利益。在这种意义上,该人格要求着超越自我的局限。同时,作为大众中一员的主体应自觉地去融入大众之中,这就意味着自我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争取自我的利益本身就是谋求大众利益的彰显。大众并不是全然凌驾于自我之上的,自我并不需要无条件地屈从于大众。冯契言:
自由的个性就不仅是类的分子,不仅是社会联系中的细胞,而且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间保持着其独立性。“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我所享受的精神境界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
自我作为大众的一员,体现着大众人格特征,尊重别人人格的同时,也要保持着自我的个性。这就是自由人格中自由的一面。平民人格也是独立自由的人格。作为平民的“我”在价值创造领域,如审美领域,依然是主宰者。诸如审美等价值创造的活动都是“我”作为主体自由精神的展现。在此意义上,审美便是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自我或人生意义的良好途径。而且,相对于其他追求方式而言,审美因为关注感性而更具有切身性,所以更能使得平民大众在生活中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主体所拥有的便是在此意义上的自由,不存在领悟终极意义的迷狂活动,人的自由来自于自我创造、自我价值意义实现的过程中。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自我与别人、大众关联,自我自由的实现一定会涉及到他人,而不是自我完全单独实现自身的能力。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特别重视“我”作为主体的能力及其实现的可能性,这与传统理想人格,如追求天道或者终极意义的圣贤、君子截然不同,而是一种现代人格范型。这也就是说,“金刚怒目”说虽然发掘了自身意义的传统根基,但还是保留自身的现代性指向。本质上,冯契此说是对传统美学的创造性整合与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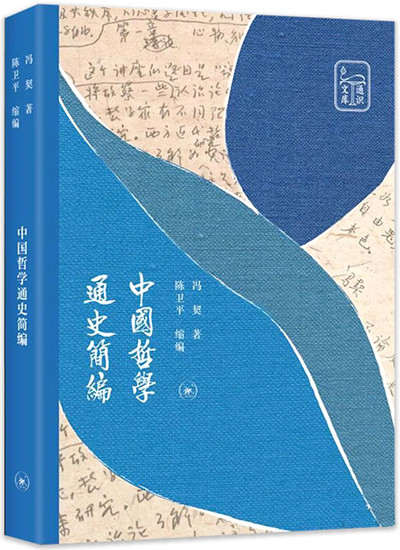
冯契《中国哲学通史简编》
四、总结
冯契“金刚怒目”说立足于美学史,同时又显示出一贯的理论逻辑,史思结合。这些是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中国传统智慧,熔铸西方哲学资源,以个性化的方式切入时代问题”所形成的一家之言,是中西马汇通视域下的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精彩个案。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设,很有必要重视冯契的美学思想。这不仅是来确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汇通融合的可能性,二者结合所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更在于通过对先生思想体系建立的过程性考察,以期获得方法论上的具体启示,即“金刚怒目”说就如何具体实现二者的结合而言,提供了一个方法指引。
*本文系2021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202108310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欢友 单位:慕尼黑大学文化研究系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2期(总第77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论冯契“金刚怒目”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美学转化的精彩个案(“艺评中国”新华号,阅读量3.9万+)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