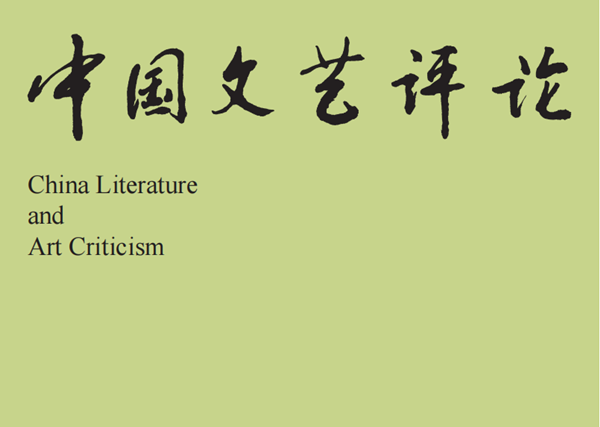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艺术是否能实现真正的艺术创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古典意义上把技术和艺术放在一起考察,并区分三种技术形态:工具、道具和元道具。固然人工智能艺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然而除非它能形成新的生产力、有真正的具身性或者能与人的想象力直接连接,自主的人工智能艺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创新能力。
【关 键 词】 技术 工具 道具 元道具 人工智能艺术 创新 具身性
一、衣服与技术
提到技术,人们一般不会想到衣服。然而衣服的确是技术,而且是与火类似、具有原型意义的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衣服也是用来辅助人类的,本身是自然之外或者非自然的存在。柏拉图曾提到,神在造物的时候,由于一时疏忽,把自然技能如皮毛、力量和速度都分给了动物,到分给人的时候,已经没有技能剩下,出于怜悯,普罗米修斯把火偷出来给了人类。
在古希腊思想中,人与技术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人本质上就是一种悬浮于自然与神之间的技术存在。人既属于自然而又因为掌握技术而有着超自然的潜能。与自给自足的技能动物不同,作为技术动物的人不可能离开技术而自存。同时技术也是区分人、神的关键。辅助人的技术给人以力量,但也标志着人的羸弱。实际上羸弱和技术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人靠技术来弥补自我欠缺;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代表着欠缺。除了人离不开技术,技术也离不开人。这是因为技术的所有存在意义都在于人。神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技术的(包括文字),而动物使用不了技术。因此技术依赖人的欠缺而存在,因此本身也是欠缺。
在文艺复兴绘画中,古希腊罗马的神总是裸体。其背后的理念并不是性开放,而是因为维纳斯她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而衣服是对其神性的否定。相反,如果艺术家画人的裸体,那可能会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关注。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第一次用世俗女性的形象来描绘神,引起朋友及委托人的焦虑。但提香很幸运,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威尼斯的确很开放。西方艺术史上第一幅真正的女性人体画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戈雅的《裸体的玛哈》。戈雅因为这幅画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差一点被烧死。总之,没有衣服的人和没有衣服的神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和概念。尽管这两者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分别,因为都是裸露的女性肌肤,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个事实:人的观察习惯总是充满着技术理性,而文化和理念也无时无刻不在规训着我们。记得学生时代的同屋研究生说他在澡堂碰见了导师,觉得很尴尬。大笑之余,我们不免会想,如果真的碰见这种情形,视而不见不是应该更正常、更符合礼节?澡堂有澡堂的观察策略。同屋的尴尬反而让人尴尬了,因为他忘记澡堂的裸体不是裸体。
二、工具与道具
作为技术,衣服存在着三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工具的衣服,即一般意义上用以保暖、遮体的衣服。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辅助常常指这类工具性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衣服是人的生存辅助,它提供温暖和基本道德自觉所要求的遮蔽。
其次是作为道具的衣服。道具衣服当然也是工具衣服,但有着一般工具衣服所不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大多数情形下,穿不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充满符号意义的社会行为,传达着身份和理念。譬如维纳斯没有衣服,这是常识意识形态;而玛哈没有衣服,这却是反常识的意识形态。当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超人电影中超人的另一个社会角色)戴上眼镜,西装革履,俨然是一个迂腐懦弱但心地善良的新闻记者。相反,在超人成为超人之前,他首先得换衣服。同样的道理,赵匡胤在成为皇帝之前,必须先黄袍加身。他所加的不是一般的工具衣服,而是做皇帝的道具。在封建社会,黄袍加身总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如今,权力的制服化是平常的技术现象,像保安、警察、军人和企业内部等有着各种各样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这些都是在道具意义上使用衣服。
道具(prop)技术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是用来直接解决问题的(那是工具技术的特征),而是用来辅助叙事的。犹如辅助导航的路标,道具是故事得以发展,意义和想象得以展开的语境设置和标识。受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关于竹马(hobbyhorse)思考的启发,沃尔顿(Kendall Walton)把道具看成是艺术哲学的核心概念,认为演员、绘画和实质上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和竹马一样的道具性质——即它们用来规定想象(prescribe imaginings)。在沃尔顿看来,和玩具、芭比娃娃一样,作为道具的艺术作品具有意义生成的能力,它们能生产虚拟真理(fictional truths), 构建虚拟世界。沃尔顿根据道具逻辑把虚拟世界分成两类:一个是游戏者个人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带有公共意义的作品世界。这是后话。

竹马
道具辅助叙事,用来生成虚拟真理。然而,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于其所叙之事或者所揭示之真理本身,而恰恰是在于道具在辅助叙事时所体现的技术形态以及其规定想象和生成虚拟真理的能力(简称“生产力”)。这中间的道理比较复杂,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修辞学道理来予以说明。我们把道具看成是像隐喻修辞上所说的喻体,但同时又借助其本体来强调艺术与修辞的差别。艺术之所以不同于修辞,至少按照艺术家孙原的说法,是因为修辞有喻体和本体,而艺术只管喻体,至于本体是什么,艺术家并不在乎。如卡夫卡写甲壳虫,至于甲壳虫代表什么,他保持沉默。甲壳虫背后的本体在于读者的解释,这不属于艺术创造的概念空间。艺术只是本体退场后的喻体游戏。用我们的话来讲,甲壳虫在卡夫卡那里是道具,是卡夫卡叙事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然而卡夫卡的艺术不在于技术手段背后的真理和目的,而恰恰在于其甲壳虫道具所体现的生产力。总之,艺术之为艺术不在于叙事本身或者叙事背后的主旨和意义,而只是在于其叙事过程中所表现的似乎是具有无限可能的技术生产力。
总之,工具技术和道具技术是人类技术使用的两种日常形态。工具技术是手的延伸(如锤子是手的延伸),而道具技术则可以被看成是心的延伸(让我们进入虚拟的甲壳虫世界)。作为心的延伸的道具技术,也是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所关注的延展心灵。他们用俄罗斯方块做例子,设想三种情形:一是游戏者只是靠自己的大脑想象来旋转方块,另一个是借助眼前的屏幕来旋转方块,再者是把游戏芯片植入大脑,直接靠芯片来旋转方块。我们暂且不谈第三种情形,而只关注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区别。在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看来,第一种情形不大可能,因为纯粹靠想象去旋转方块远远超越了人脑所能承受的计算能力。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情形中的屏幕辅助则是把想象空间从脑延伸到指尖,可以在线导引手的运动,从而减少人脑几何想象的“计算瓶颈”(computational load),并由此构建一种具有足够娱乐效用的游戏空间。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俄罗斯方块看成是工具性游戏,那么作为延展心灵的屏幕则是沃尔顿意义上的道具。作为工具的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作为道具的技术则是意义和想象的延展。道具技术的意识形态意义则正依赖于道具在建立具有延展意义的心灵和想象空间方面的作用。
三、红披风
在超人电影中,超人的红披风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衣服技术。首先超人的红披风依然是一般意义上的衣服,它是超人的衣服,因此是工具衣服。其次,红披风也是道具衣服,因为它规定我们的想象——穿红披风的是超人,而不再是迂腐懦弱的肯特。
然而,红披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规定我们的想象,而更在于它改变我们的想象。这听起来似乎是同一回事,因为规定应该包括改变。然而在实际语境中,当目前的语境是围绕着作为新闻记者的肯特而构建时,为了让肯特变成超人,而且能让观众明确地跟踪这种改变,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道具,它能在一瞬间改变整个语境和意义的空间。这就是红披风的技术意义。在电影中,在超人出现之前,一般都需要肯特先进入电话亭,进行一个华丽的转身,然后红披风在肩,于是才有了超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在语境之间进行切换的具有元意义的道具:当肯特穿上红披风,他和观众进入超人的世界;而当超人脱下红披风,他和观众又回到肯特的世界。

电影《超人归来》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元宇宙的角度看,红披风是一种宇宙穿梭机,它可以在瞬间实现世界和想象力的转换。这显示红披风有着与一般意义上的道具生产力(即沃尔顿所说的“道具能生成虚拟真理的能力”,或者孙原所说的“喻体生产力”)不同的整体性生产力,即它能生产整个世界,而不单是生成具体行为或者事件的能力。比如在日本山林里,我们常看见牌坊式的鸟居门(torii gate)。在神道教那里,鸟居门的作用类似于超人的红披风,一旦进入,就是神灵的世界。因此要行净礼,用木勺舀水洗手,然后方可进入。
我们把红披风所代表的技术理念称作“propropic技术”(而“propic技术”则是道具技术)。它所表现的生产力不是工具性技术所代表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不是道具性技术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构建具体行为和事件的能力,而是转换整个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整体性创新能力。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技术或者艺术家作品才具有这样的元道具性(propropic)的创新能力。
我们以大家熟悉的火为例,来说明这三种技术形态的差别。火作为自然现象为人类所掌握,成为人类赖以生存、改善环境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火的使用标志着技术的开始,是人成为人的根本性进化事件。但从纯技术角度而言,自然火的使用依然只是工具使用,谈不上更复杂意义上的文化和技术应用。这是火技术的第一形态:火是工具。只有当人类步入宗教文明,火的使用才开始复杂化,呈现出作为工具火所不具有的意义生产力。比如在人类的宗教文明中,火具有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作用——它是净化、去秽的道具。比如《荷马史诗》中多次提及的围绕火堆所举行的盛大葬礼仪式,它是由生命和财物的焚毁和充满油脂的烟火升华所导引的关于死亡和凤凰涅槃的想象。作为道具技术,祭奠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火堆犹如俄罗斯方块的屏幕,它构成了辅助阿喀琉斯思念密友的特定的场景和意义空间,也使得史诗中充满想象和仪式感的行为和叙事得以展开。这是火技术的第二形态:火作为道具技术,它在观念意义上呈现喻体(灵魂的净化和升华)和第二自然(死后的世界),并由此生成想象和虚拟的叙事世界。
而火的第三技术形态,即火作为整体性的创新技术,需要等蒸汽机的出现方才成形。在1750年以前,人类生产和生产关系所依赖的能源形式主要是风、水、火(作为工具的火)和动物的自然技能。而蒸汽机的出现则改变了一切。蒸汽机是火和机器的一种连接,即火机接口,但本质上还是火。它不再把火当作工具来直接使用,不再直接用火来改变自然,而是把火所生产的热能转化成机械能,再用机械能来做功,执行工具技术的功能。
蒸汽机所代表的能源理念和火的运用,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改变了人类世界。蒸汽机让工厂的设置和规模大小开始脱离自然资源的束缚(如不必总是接近水源),促使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工厂导致城市出现);而人类靠蒸汽船的发明也开始远渡重洋,去征服和掠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随之出现。总之,蒸汽机的出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新的工具、某一特定的新生产力,而是一个能生产整个新世界的创新技术。
假设一个外星人在屏幕上观看人类发展史,当他看见蒸汽机的出现,他就应该明白后面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类由此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蒸汽机的作用就好像鸟居门、超人的红披风,它们代表各自不同类型的宇宙切换。每一种技术固然在一开始都是新的,但只有个别技术和艺术作品在出现的时候才具有创建整个新世界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蒸汽机在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被看成是红披风式的“propropic技术”,它的出现代表着整个世界的转型和切换。
四、技术与创新
我们借助工具、道具和元道具的概念来讨论技术创新,然而技术与创新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工具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然而新技术也是旧问题、旧的社会关系自我延续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新技术的创造可以是创旧而不是真正的创新。其间的关键是技术所改变的对象:技术所改变的只是问题的解决方式,还是进一步改变了问题本身或者背后的游戏规则? 如果问题和游戏规则保持不变,那么新解决、新作品、新文章和新艺术都只能说是用新瓶装旧酒,谈不上创新。
比如在冷兵器时代,杀人用刀,后来用枪,但枪的出现只不过是杀人的延续,可以被用来杀更多的人。它本质上是对旧问题的新的解决手段,本身不带有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潜能。在这方面,枪和蒸汽机在创新能力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技术形态:一个是新工具的创旧,让旧问题得到了新解决;一种是全新的、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元道具。
技术的新和技术的创新常常被混为一谈。创新是生产力概念,而单纯的新技术可以是旧生产力、旧生产关系的延续,常常也正是旧生产力、旧生产关系得以自我延续的手段。如新能源汽车至多只是旧的汽车工业的延续,在宏观意义上谈不上创新。而在创新概念内部,我们也需要区分道具创新和元道具或者整体性生产力的创新。道具创新一般涉及新喻体、新媒介的发现发掘(如现代艺术对颜色和线条的研究),也关系到虚拟真理或者意义本体的生产能力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模式的建构(如NFT、数字货币等)。这些都是技术创新的一面,但其意义也不能被过分夸大。
于是我们需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创新概念:一是工具创新。工具创新是一种纯手段的创新、一般不涉及目的和观念的革新。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纯工具创新实质上更是创旧,即用新手段解决旧问题,从而也构成旧问题的自我延续。第二种创新是道具创新,涉及艺术在利用喻体或道具进行叙事时所体现出来的技术生产力。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道具不仅能强有力地规定人的想象,也能在特定空间内靠道具的技术运用生成无限的意义和隐喻本体。道具创新尽管意义有限,却也是艺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尽管它不总具备革命性,但至少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纯粹的工具新或者创旧。在真正的艺术家那里,我们常常能发现具有独特虚拟生产力、能触及以前触及不到的生命本体经验的技术能力。如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于1964年拍摄的《红色荒漠》,它之所以被称为“第一部彩色电影”,不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彩色电影,而是因为该电影使用色彩的方式已经脱离了物理表面的空间限制。它用色彩来表征情绪和情感,如用红色代表恐惧和压抑等,颜色在安东尼奥尼那里变成了内心情绪的延伸。这部电影的历史意义也主要表现在它在道具意义上对颜色生产力的重构。第三种创新是元道具创新。这是划时代、带有革命性的创新。元道具创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道具意义上的真理或者本体的生成能力,更涉及整个艺术和技术世界的切换。作为红披风式的元道具,它能把我们从一个世界带入另一个世界。因此它所规定的不仅仅是想象,更是我们想象的改变。在这里我们把想象看成是一种观察习惯,那么元道具能改变的则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比如戈雅的《裸体的玛哈》逼着我们第一次看到并承认裸体,它以一种无可逃避的方式使我们直面人性和现实。福柯所推崇的委拉斯凯兹(Velasquez)的《宫娥》也具有类似意义的观察改变。在福柯看来,《宫娥》中的画家本人直视着观众:它让观看变成凝视,让凝视突破了历史和画框,从而以一种令人战栗的狱卒般的眼神规训着时间和未来。
五、人工智能艺术
利用前面的概念铺垫,我们这里可以简单评价一下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又意义深刻的问题:人工智能(AI)是否能创造艺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语义纠缠(譬如什么是艺术?),我们先从创新角度来评价AI艺术的本质。目前也正是由于AI艺术的新,加上其技术本身所承诺的各种可能,很多人对人工智能艺术产生迷惑和误解。AI艺术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技术性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由暗箱支持的透视法艺术),一方面在于它是独立于人的相对自主的技术,另一方面它能自主创造目前能被艺术市场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在这两方面中,第一方面即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不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前面说过,技术至少在原则上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目前的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的确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它同时却是弱智能,而不是强智能(AGI)。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能自主地处理现实问题,而只能在封闭条件下处理和分析数据。换句话说,它们不具备处理现实问题所要求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人工智能艺术的出现似乎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它在向世界宣示,人工智能已经迈入了最需要创新的人类智能领域,那就是艺术。因此,分析人工智能艺术的创新性,不仅仅能加深我们对创新和相关技术形态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人工智能艺术是否真的预示着AGI(通用强人工智能)的到来。
自主性人工智能技术,如无监督深度学习能够做很多人类以前无法做到的事,也可以解决很多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更精确的人脸识别、蛋白质折叠结构的预测描述、轻松打败围棋世界冠军等。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惊人成就下面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相当有限的。除了本质上是加减法运算的强力工业计算和梯度下降等特殊算法以外,机器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并不能超越在输入数据中寻找统计性的关联。机器既没有意识也不具有道具逻辑所要求的想象和类比推理能力。这意味着机器只能像绞肉机绞肉一样“自然”地、机械地去处理数据,把数据当作由算法所事先规定的“既定对象”。也就是说,对于机器而言,数据就是数据。它无法把数据看成像喻体或者道具一样的东西。
AI的惊人成就和其背后的能力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单从成就而言,AI的能力似乎深不可测。然而这其间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大数据的收集和由工业实现的暴力计算。细节之外,我们只需了解AI与数据之间存在的某种矛盾性关系。一方面,AI需要海量数据来训练自己。这本身不是坏事,相反它似乎表示机器之于新事物所具有的开放性——它能处理远远超出人能处理的数据信息。机器对数据的开放性,似乎正是机器走向创新的前提条件。然而另一方面,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真正开放的系统在纳入新事物时所应该具有的灵活性和低成本期待。也就是说,真正开放的系统应该在欢迎新事物的同时不会造成内部的过度震荡。如果任何新的输入都有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崩塌或重构,这个系统就不可能是真正开放的。有大量证据证明,目前的人工智能通常是不稳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深度神经网络接收到的数据的微小变化,就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变化。……改变图像上的一个像素,AI就把马识别成青蛙。”
新的数据输入有可能造成整个AI系统高成本的重新训练。这种带有矛盾性的机器—数据关系说明,AI本质上只能稳定地处理旧数据,而在其输出层面上的新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保守和自我封闭的能力。前面我们提到机器无法把数据看成道具,而只能以纯工具(绞肉机)的方式去处理数据。这里所说的机器悖论以及其所体现的“恋旧”,与工具创新本质上是创旧的说法相吻合。
譬如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转导推理就是这种典型的从“旧”(已观察)到“旧”(已观察)的算法。与归纳推理从个别(个别是旧的)到一般(一般是新的)的推理不同,转导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在模型训练之初,机器已经观察到训练集(带标签)和测试集(不带标签)。一开始它不知道测试集的真实标签,但可以从其特征分布中学到些额外的信息,靠概率分析来确定输出。这种推理本质上是从已知到已知。前面所说的深度神经网络中的新—稳悖论对转导推理也同样适合:一旦新样本进入,转导模型就得重新训练自己。
从这个角度看,自主性AI并不具备真正的创新能力。这包括看起来极其富有创造性的机器学习。如在深度神经网络中,把在图形识别上训练的模型跨领域用到国际象棋,四小时就能学会从没接触过的116个国际象棋概念(反复训练1680000次——128000步开始收敛,1680000步映射关系清楚),并知道什么是威胁、弱势。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般性定义每个新概念为映射,列出棋盘不同的权重,训练就能在A与B原来两个不知道的事物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形成新的概念。这个成就固然了不起,但它实质上还只是重新发现已有的联系,本身并不包含或者体现真正道具意义上的想象和创新能力。
再譬如蛋白质折叠结构预测,原来只能四年识别一种结构,现在两个月能识别一种。它大幅节省时间,从而加快了技术进程。这会不会导致像蒸汽机一样的技术革命,导致对人类生产关系的重构?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即使这个技术被证明具有创新能力,它也只能以辅助形式出现。如何利用技术的时间效应去重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是技术本身能做到的。即使是蒸汽机的创新能力,它也只是在人的富有想象力的应用中得以实现。
在艺术领域,AI的作品本质上也是如此:它无非是对图像进行工具性的处理然后导出输出。如上面这幅作品《埃德蒙顿•白乐弥的画像》(Portrait of Edmond Belamy),是向算法输入不同时代的一万五千多幅肖像作品后由算法自主生成。该作品在2018年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3.2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埃德蒙顿•白乐弥的画像》(来自Wikimedia Commons, the free media repository)
更多的人工智能艺术作品如谷歌的《盗梦空间》(Inception)也是凭借类似海量的数据输入然后由机器自主生成。这些自主机器所依赖的算法本质上可以被称作“切割迁移”,其关键是机器不能真的像人那样靠想象、靠类比等道具思维来生产作品,而是靠工具性的算法分解、转移已有特定类型的数据特征并按照机器所理解的分类标准来重构一个特征型。

《盗梦空间》(来自Wikimedia Commons, the free media repository)
六、普特南问题
前面所说的问题看起来仅仅涉及过程。如果AI能产生艺术并且能为艺术市场所接受,为什么要在乎艺术是怎么得来的?“切割转移”和道具想象有什么样的实质性差别,导致我们怀疑AI的创新能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普特南式的问题。
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的开始,普特南曾描绘一只蚂蚁在沙滩上爬行从而勾勒出丘吉尔图像,他问这个图像是否具有指称?是否真的是丘吉尔的画像?这个问题实际上具有一般性(不仅仅涉及指称),并且涉及到艺术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假设某岩石上自然呈现出公牛图形,而且和毕加索的某幅公牛图一模一样,它是不是艺术?算不算创新?普特南强调沙滩上的丘吉尔不具有丘吉尔指称,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与丘吉尔这个人有任何因果联系。一个与丘吉尔没有任何因果联系的图像,即使你把它看作是丘吉尔图像,也不是丘吉尔图像。同样的道理,一个与公牛没有任何因果联系的公牛图像,即使它看起来像是公牛图像,也不是公牛图像,更何况是毕加索的作品。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个道理说明,艺术和艺术创新都离不开与现实生活的因果联系。而道具和元道具恰恰都是由人类生活所特定呈现的、经技术的参与而造就的人类精神现象。离开了道具和元道具,纯粹工具性的生活固然也算是人类生活的特征之一,但只有在道具以上的理性空间中,我们才能真正发现艺术与创新。人工智能机器只是作为工具被纳入了人类活动的范围,犹如沙滩和岩石,但它们都不知道什么是道具。蚂蚁不知道沙滩上的印记可以不是印记,而可以用来表征某英国首相;气候也不知道岩石可以是画板或者屏幕,可以用来表征牛羊。因此单从结果上来看艺术和创新,不仅仅是不理解艺术和创新,更是不理解人类生命与艺术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七、创新是二阶概念
总之在技术创新上,我们要区分创旧与创新。这并不是故意把创新定义得过窄、标准设置得过高以证明我们的论点,而是因为工具创新往往只不过是同一种技术范式的自我延续、同一种技术的时空平移。相反,真正的创新,它在本质上体现着与人类生命的因果联系,特别是在道具意义上反映着人类精神的想象和自由。
同时,生产力的革命并不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技术革命总意味着社会或者人类知识的革命,并且以后者为前提。相反,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态势是自我延续,而不是自我更新。像澳大利亚土著人生存栖息一万多年,一直被冻结在结绳、无文字、没有知识积累和文明进步的原始社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和外界缺少接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技术本身所普遍具有的惰性和冻结历史的能力。这种由技术所造成的难以逾越的文明陷阱,是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现象。一方面没有技术是不可能创新的,另一方面技术本身又不可能自主自发地创新。其间的张力说明技术在本质上只能以各种辅助形式扮演着社会和技术革命的角色。
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衣服。衣服何尝不是如此?作为工具技术,衣饰风格可以与某一人类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到达超级稳定的同构性耦合,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把几乎所有的衣饰创作限制在狭窄范围内。而衣饰的道具使用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以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等手段来维护和巩固这种技术和风格垄断,使创新成为不可能。相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衣饰改革,可以在一瞬间实现社会革命,像超人的红披风使肯特从一个平庸的男人变成超人。这之间不免有着历史变革本身所具有的戏剧和夸张,但背后的逻辑却也不断地被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这类历史事实所映射。
超人的披风在一个很深刻的意义上是“具身性”(embodied technology)技术,它不是一般的道具。超人不可能没有披风:一旦脱下,他就变回为肯特。披风的生产力恰恰表现在它能定义肯特和超人的分别。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思考技术创新: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不仅仅要求技术是手或者心灵的延展,更要求技术延展到身体和心灵(即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所说的俄罗斯方块的第三种玩法——把芯片植入大脑,然后直接靠芯片来旋转方块)。具身性技术不再是外在的工具或道具,而已经延展到人的身心,包括其语义、语法、情感和想象力的空间。毕竟,只有当技术与人类身体和人类想象力直接连接在一起,技术方才具有真正的大规模创新能力。也就是说,作为想象力的辅助,创新性技术应该具有具身性。
比如蒙古人的马。蒙古人改变世界史的能力离不开其使用马所展现的特殊技术形态。马对蒙古人而言,不仅仅是外在工具,更可以说是蒙古人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当蒙古人骑着马穿越欧亚大陆,对外人而言,他们似乎就看到了古希腊人所想象的半人半马。马作为外在工具已经延伸到蒙古人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对蒙古人而言是具有具身性的技术。而一旦技术有了具身性,人就成了赛博格。
总之,只有当具身性技术延展到人的身体和心灵,技术才能够变成一种富有创新和革命能力的生产力,它才可能改变整个生产关系。相反,仅仅是工具性的技术使用,在原则上是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艺术,它能做的只是风格迁移或者元素重新组合,本身不包含任何想象力的重构和发挥。我们把人工智能艺术的创新叫做“创旧”,即使它生产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但在本质上它还是属于自然,而不是属于艺术。
“创旧”这个概念说明,无论一个技术产品或者艺术生产形式是多么新,它骨子里可以是保守和维持现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创新”是一个二阶概念。在一阶意义上,无论一个技术怎样新,或者看起来如何富有创新能力,这一切都可能只是表象。作为二阶概念的创新,它所指的不仅仅是时间和认知意义上的新,而是指新技术所代表的新生产力。当技术有了道具性,并且可以与人类的身体或想象力直接连接,被赋予了一种二阶能力,它可以为我们拓展一个新的语义和语法空间,从而重构出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这就像前面所说的“超人的披风”,一旦披上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总之,我们必须要从二阶意义上去理解技术创新与革命。
相反,如果把技术或者人工智能只当作一阶的、纯粹工具性的技术,它反而可能会扼杀艺术。比如好莱坞电影自从爱上CGI(computer graphic image,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以后,它似乎就失去了创新能力,大部分电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炫技。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人工智能这种前沿技术所带来的耳目一新而失去艺术之为艺术的生命本源。新技术看起来是新的,但它也可以扼杀创新,让我们在期待中走向冻结我们的深渊。
作者:朱锐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5期(总第80期)
责任编辑:易平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工具、道具、元道具:人工智能艺术的技术本质及其创新能力(“艺评中国”新华号,阅读量3.6万+)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