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长篇小说《敦煌》:
用虚构笔法“活化”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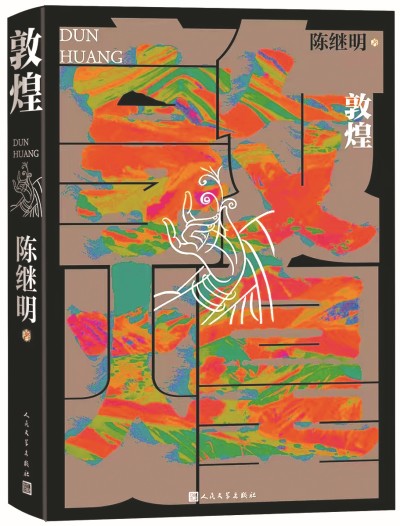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敦煌是一个知识性的、文化遗产的、充满底蕴而又遥远神秘的存在,似乎它是已经固化的文化遗存。然而,敦煌曾经是真实历史中的边陲重镇,也同样鲜活地延续到现在。无数代的人们在敦煌生活、劳作、繁衍,敦煌的样貌和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种种变迁。它的文明一度长久湮没在主流视野之外,直到近代才被西方探险家发现,也遭受了被掠夺与破坏的厄运。
关于敦煌的作品有很多,但主要集中在非虚构领域或学术领域。文学与历史学、博物学、考古学不太一样,文学的价值在于把写作对象“活化”,赋予它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中国拥有如此广博丰富的历史,但本土作家对历史的书写、对文化遗产的发掘仍稍显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继明长篇小说《敦煌》的问世尤其令人振奋,这是一部用虚构小说笔法书写敦煌的重要作品。《敦煌》融合了“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空廓豪迈,与“角声吹彻梅花,胡云遥接秦霞”的慷慨悲怆,形成了一种粗粝、大气、恢宏、壮阔的语体风格,这部小说把敦煌“活化”了。
三条线索与两个时空
谈到“活化”敦煌,首先要从作品的叙事线索和故事时空谈起。《敦煌》分为三条叙事主线索和两个故事时空。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了唐初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分成三条叙事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宫廷画师雪祁三次进入敦煌的过程,第一次去是学画,以及搜集情报;第二次去是造窟造像,画壁画;第三次去是寻找诅咒窟的谜底并定居。这条线索非常完整,背后隐藏的逻辑是唐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交流史,实际上就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亦即中原儒道互补的主流文化与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等文化之间的交往。
第二条线索以慕容豆(汜丑儿)为中心,他是吐谷浑部落的一个落魄贵族,被打败后带着残兵来到敦煌天水村。吐谷浑原来可能是鲜卑人,鲜卑人起源于东北,生活在中国的北部边疆,后来经过远距离的迁徙来到西部地区。这些残兵在慕容豆的带领下,对整个村子进行大规模的惨烈屠杀,仅把女性和小孩留了下来。他们学习汉人耕田的方式,改换成汉人的身份,希望保存实力,以图复国。这条故事线索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最终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最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第三条线索是令狐家族的故事,这是敦煌日常生活和造窟的故事。日常生活有着强悍的连续性,构成了“传统”的载体。也许我们很难回忆清晰祖父一代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的文化积淀和集体记忆、情感模式和爱恨情仇,从唐代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化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原型部分,一直延续了下来。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如企业家、作家、官员、学者等,但中国人内心基本的文化原型和认知世界最根本的方式并没有多大的差异,这是日常生活书写线索背后的逻辑。
以上三条叙事线索同属于唐初的历史时空。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个属于当下的时空,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陈继明本人也出现在这个时空里面,所以这部小说带有一种元小说的色彩,或者说非虚构的色彩。小说中还运用日记、文件等形式,给读者带来一种似真感,好像这是上世纪刚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空中,出现了一个人物“慕思明”,他自认为是吐谷浑的后裔,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诗人,后来在90年代经济大潮中下海成为富商。这背后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转型的大背景。慕思明是文化寻根者,他要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文化的来处,寻找历史的根源。成为商人之后,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这是属于当下这个时空的叙事线索,也是整部小说的情感结构。
因此,在陈继明笔下,敦煌从知识性的、文化遗产的存在变得血肉丰满,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和记忆息息相关。
精神追求与大唐气象
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来说,他们生长于斯,由于外部艰苦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这使得他的求生意志变得尤为强烈。在《敦煌》中,这种求生意志体现为吐谷浑部落到处寻找、不断开拓自己生存的空间。尽管这个过程也显示出某种残忍的、野蛮的气质,然而还原到特定历史环境中,我们可以理解其为了族群绵延的合理性。因此,绿洲求生意志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是有超出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层面。在生存的底部还有属于精神的东西,那才是人之为人的证明。人在基本生存之外,在现世生活之外,还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寻找心灵的信仰。
历史上留下著名石窟的地方,像洛阳龙门、大同云冈、天水麦积山以及敦煌,这些地方或是四战之地,或是生存环境特别艰难的戈壁沙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否则无法支撑下去。《敦煌》的求生意志就体现在这个层面,它是包含着复杂矛盾的辩证结合体,既有本能的动物性的、野蛮进取的一面,也有追求宁静、追求超越性的精神层面,这才能使得我们的文明不断延续下去,不同的文化因子才能接纳彼此,然后融入彼此,从而构成新的文明的基体。
再来谈一谈大唐气象,一直以来,人们对大唐气象的论说数不胜数,如同过江之鲫。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诗《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其中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唐气象实际上就是万国来朝,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影响力。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虽然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有别,但唐朝得到众多国家的拥戴,成为东亚共主。在这种情况下,大唐允许各种各样的文化同时存在,让不同的文化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展现出生生不息的魅力和活力。文化自信正是要有一颗包容之心,不恐惧、不排外,能接纳和吸纳,有信心让不同文化都呈现出自己的美,美美与共才能达到天下大同。这是大唐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敦煌》给我们的启示。
认识历史与认识自我
关于如何认识历史这个问题,《敦煌》给出的答案是“古今无不同”。古代与现在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差异巨大,但这个差异更多体现在器物和制度的层面,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似乎并非如此。这就涉及我们怎么看待历史的延续性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发生过断裂的文明连续体,历史的延续性就体现在文化上,只要文脉还在,血脉就还在。
关于如何认识自我这个问题,《敦煌》给出的答案是“你我无不同,人我无不同”。无论我们之间存在阶层、族别、血缘、地缘、身份、语言、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个体的人就像尘埃,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群体的人类的存在。
作品还讲出了“同”中的“不同”,也就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变。这体现在后来的文化继承者如何面对“同”,创造出自己的“异”,即自己的创新性。小说中主要的主人公画家雪祁的故事表达的就是这个隐喻。雪祁从小是绘画天才,他不断锤炼自己,接受新鲜的经验、不同的文化,提升自己的技艺,扩展自己的认知,最后找到了超越于行画的、独创性的东西,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创作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雪祁和小说中的人物“陈继明”、现实中的作家陈继明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创作者,都在用线条或文字进行新的文学艺术空间的建构。在《敦煌》这部长篇力作中,陈继明给出了自己对敦煌的创造性的解读和写法。作品的独特性在于作家用自己极具想象力的方式“活化”了敦煌,让敦煌不再只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成为了一幅波澜壮阔、激荡人心又极富启示的生活画卷,流淌在每一位读者的心间。
(作者:刘大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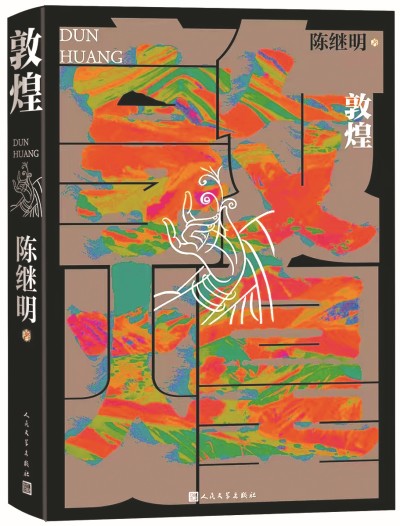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