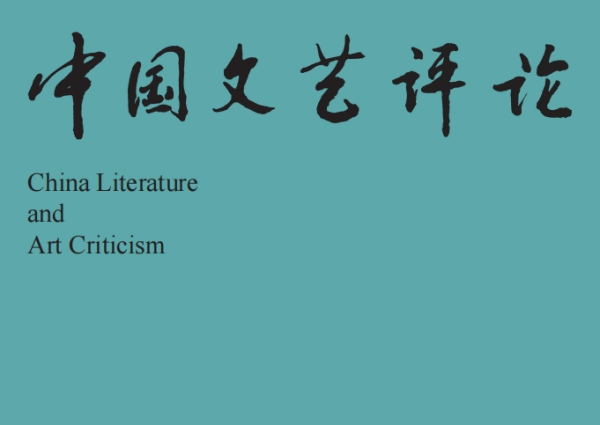
【内容摘要】 “意象”是重要的哲学美学范畴,也是一个极易产生语言歧义的理论范畴。常见的混淆是将哲学美学与心理美学意义上的意象、哲学美学与诗学意义上的意象混淆起来。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意象范畴的哲学美学内涵。“意象”作为一个标示哲学美学本体意识的范畴,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是中国古代尚象重象思维的体现,是中国古代诗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意象具有圆融性、生成性、超越性、情感体验性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基本特色,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审美视野中。
【关 键 词】 意象 哲学美学 心理美学 诗学 中国传统美学
“意象”是重要的哲学美学范畴,也是一个极易产生语言歧义的理论范畴。有一位外国的文艺理论家将“意象”称为一个“灵活得令人困惑的术语”,他针对的是“意象”这一术语在西方美学文论中的运用。西方文论界和美学界关注“意象”是较晚近的事,而对于中国美学来说,“意象”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哲学美学范畴,内涵要广阔复杂得多。意象理论和意象问题虽然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要说清楚什么是“意象”,说清楚意象理论对于中国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学术界,关于“意象”范畴的语义内涵存在着诸多讨论,也存在着诸多混淆,最常见的混淆就是将哲学美学与心理美学、诗学意义的意象混淆起来,这些问题不解决,则难以把握意象作为一个哲学美学范畴的语义内涵。
一、“意象”范畴的哲学美学与心理美学的区分
对于“意象”美学研究,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是将“意象”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从审美心理学意义上进行阐释。这一倾向的形成受到西方意象理论影响。“意象(Imagery),人脑对事物的空间形象和大小的信息所作的加工和描绘。和知觉图象不同,意象是抽象的,与感觉机制无直接关系,精确性较差,但可塑性却较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意象”的这一解释,显然是将其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术语看待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也认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另外,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美学日益重视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的研究,这不仅影响到西方美学对“意象”的理解,也影响到中国当代美学界对“意象”的理解。中国当代美学界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意象”理论研究,将“意象”作为一种心理事实看待,重视“意象”与美感经验的关系。这一研究传统始于朱光潜。朱光潜将美(意象)看成是主体心理和意识的对象,从美感经验的角度阐释意象,主要依据的是来自西方的克罗齐的“形象的直觉”和利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移情理论,它的最大特点是将文艺的创造与欣赏当作一种心理事实去研究。不过,朱光潜并没有直接将“意象”作为审美心理学的本体论范畴,用以阐释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规律。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一些美学家则明确将“意象”作为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核心范畴,从美和艺术本体的意义上来阐释“意象”范畴。比如,汪裕雄明确提出“审美意象可以看作审美心理的基元”的观点,从审美心理学角度对“意象”予以完整的理论界定:“美感起于对审美对象——美的事物或现象的直接观照。感知所得的表象,经由想象的作用,被再造,被重组,渗入主体的情思,融汇进主体的理解,就是审美意象。主体因意象的孕育和诞生,因对意象的玩味和体验,而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满足。审美意象的孕育、生展,贯串于美感心理的全过程”;顾祖钊在其理论代表作《艺术至境论》中以知、情、意三种心理功能区分为依据,将艺术形象的创造划分为典型、意境、意象三种艺术形态;夏之放将意象看成是文艺学体系建构的第一块基石或逻辑起点,他说的“意象”即是在过去已积累的大量表象的基础上,主体头脑中新生的、超前的、意向性的图像,亦是充分体现艺术家想象能力和情感意志能力的心理意象,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胡经之提出了艺术思维不是概念思维,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形象思维,而是意象思维的观点。有的学者还明确提出“从学科性质来说,审美意象属于文艺心理学的命题”的观点。这一切都说明,从心理学意义上阐释和理解“意象”成为中国的意象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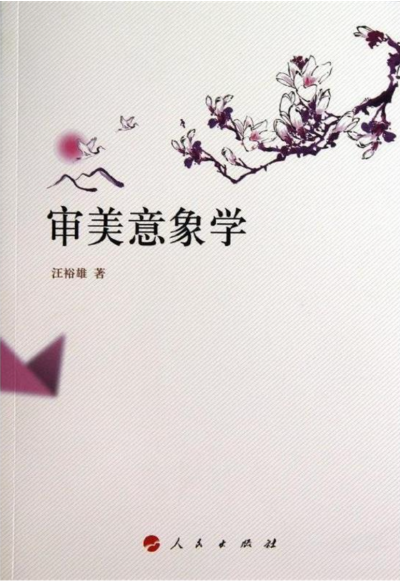
汪裕雄著《审美意象学》
相对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研究思路,“意象”创构作为一种美感经验和审美心理性质的考察,的确丰富了意象理论的美学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哲学美学和艺术本体论意义的“意象”范畴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阐释可以等同起来。这是因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主要是从人们的心理经验即知觉、表象、情感、记忆、想象等方面加以阐释,是人们的心理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与投射,这种反映与投射不一定具有审美意义。重视从审美心理学角度阐释“意象”的学者,或者如顾祖钊那样,将“意象”阐释为心理表象一类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将意象分为知觉意象、记忆意象、想象意象三类:知觉意象即在知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感性形象,记忆意象(记忆表象)即感知过的事物在脑中呈现的形象,想象意象(想象表象)即有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过的新形象;或者如夏之放那样,在表象心理学的基础上谈意象,认为表象是过去已经经历过的事物在记忆中留下的映象,意象则是在过去已积累的大量表象的基础上,主体头脑中新生的、超前的、意向性的图像。产生新意象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则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性想象。这样的意象阐释与分类即使针对的是艺术和审美,由于它所描绘的心理特征也适合一般认知活动和思维活动,并不一定能切中意象的审美本质。克雷奇等人所编的《心理学纲要》把意象区分为记忆意象(memory image)和创见意象(created image)。记忆意象是指对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的,等等),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曾经作为一种刺激存在过,但现在并不存在于知觉领域之中。当我们要描写自己儿时住过但早已倒塌的房子时,俨然看见它,这就是一种记忆意象。创见意象则是对一个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的及其他),而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从没有作为一种刺激实物而存在过,它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客体。一位作家当他琢磨着下一个情节时,俨然看到他的主角,尽管这个主角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在地球上出现,这就是一种创见意象。创见意象是以记忆意象为基础,与想象力相联系的。克雷奇的这一意象分类就与顾祖钊、夏之放等基于表象心理学的文学艺术意义上的意象分类有相似之处,重视想象、创见的因素在意象生成中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涉及到“意象”的审美创造和情感体验的因素,所以还说不上是审美意义上的“意象”。在西方现代认知科学和思维科学中,“意象”亦被作为重要概念看待,它包含着知觉、想象、记忆表象与认知等心理因素。与以概念、语词为基础所形成的思维活动相比较,意象思维无疑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和具有创造性的思维形式,它对于科学家思维过程的发生非常重要。比如,爱因斯坦谈到自己进行科学研究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在我的思维机构中,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地’再生和组合。……这种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这种思维体现了科学认知活动的主动性与创见性,但并不一定具有审美意义。如果它缺乏审美主体那种情感体验和关注,不能将知觉和想象中的东西提升到符合审美理想的高度,就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审美意象的创造。比如,白居易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人们之所以将它视为审美意象,不只是在于它写出了人们心理活动中所知觉和想象的东西,更在于它按照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将知觉和想象的东西理想化、情感化、诗化了。近年来,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关于“意象”图式的研究也很活跃。意象图式是人们与现实世界感知互动中所获得的基本认知结构和组织模式,意象图式论中所说的“意象”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心理表征,具体指在没有外界具体实物刺激的情况下,人们头脑或心智中仍然能获得某人或某物的印象与形象,也可能构成一种富有想象和创见的心理活动,但这并非是针对审美而是探讨意象图式与心理认识的关系。
重视“意象”审美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有的并不排斥“意象”范畴的哲学美学研究。比如,汪裕雄以“意象”聚焦审美心理时就没有简单地将审美意象的研究还原为心理事实,以审美心理的研究取代哲学的思辨。他说:“直观体悟的哲学和美学,正要求把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辨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就是说,要采用‘哲学—心理学’方法。这一方法,也就铸就了美学的中心范畴——意象。”在他看来,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正是这样的典范著作,它是“以康德到克罗齐的哲学美学为基本骨架,以审美经验的心理描述为活的血肉,既使哲学美学落实到具体审美心理现象的层次,减少了它形而上的抽象性和空疏性;也使心理学在理论上有所归依,避免了经验性描述的散漫性和凌乱性”。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中西“意象”理论哲学审美和心理审美之间的不同,认为西方美学的“意象”(image)及与之相关的想象问题,“是从感性与理性、形而下与形而上两分的立场出发的,所以虽承认image和想象可以充当沟通感性和理性的桥梁、纽带,但仍将其划归经验感性层面,放在心理学领域加以处理”,而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则不一样,历来是物象、兴象(含喻象、象征、典故等)乃至于指称“道”的大象(象罔)的总称,既涵括具象的形而下的“器”,又指涉恍惚无形、形而上的“道”,同时还深蕴人心的情和理,所以更具有哲学审美意味。不过,就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意象的心理美学分析的基本倾向来看,是受西方心理美学方法的影响,将意象作为一种感性形象看待,重视对意象的心理要素与特征的分析。而在笔者看来,“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提出,本质上是不同于西方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理论的。叶朗根据中国传统美学的情景交融说并结合现象学美学思想来规定美的本体,认为“审美意象”不同于西方学者在认识论和心理学领域中使用的“意象”(image)这个概念,后者是感官得到的关于物体的印象与图像,是一种心理意识的体现,而“审美意象”则是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他还强调他的“意象”论是存在—本体论和精神价值论的统一。这些观点对于理解“意象”范畴的哲学美学内涵具有方法论意义。它说明,对于“意象”范畴的理解决不能停留在意象的感性形象和心理经验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要进入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层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意象范畴的美学价值,使它进入到当代人的审美视野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和光彩。
二、“意象”范畴的哲学美学与诗学的区分
“意象”在西方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18世纪以来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艾布拉姆斯对“意象”(imagery)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它有三层含义:一是“表示诗歌或其它文学作品里通过直叙或暗示,或者借助于比拟使读者感受到的形体或特性”,如华兹华斯的《露西》就属于这类意象诗的典范作品;二是“代表对可见的客体与情景进行的描写,尤其是生动细致的描写”,如他所例举的柯勒律治长诗《古舟子咏》中的诗句:The rock shone bright,the kirk no less,That stands above the rock;The moonlight steeped in silentness,The steady weathercock(山石在闪烁,还有那耸立在山石上的教堂,月光如水,寂静无声,沐浴着高扬的风标);最后一层意思即“意象”等同于比喻,尤其指暗喻和比喻的比喻物(喻矢),他认为这是新批评理论常见的理解。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论界对“意象”的关注,首先也是从诗歌和诗学领域开始的,它与白话诗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朱自清说,白话诗的创作“最大的影响是国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西方诗论特别是英美意象派诗论。胡适总结自己的白话诗歌写作经验时提出“影像”(意象)说,明确认为它与“近代西洋诗人提倡的‘imagism’(影像主义)”是一回事。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杂志开设“意象抒情诗”专栏,徐迟、邵洵美、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对西方意象派诗歌作品进行译介并宣扬其理论主张,他们普遍认同意象派诗歌的客观化特征和象征品格,并将其与浪漫主义重视主观抒情的主张对立起来。这种宣扬与主张亦推动了“意象”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在中国诗歌理论界的传播。意象主义专注于一种神秘的诗歌经验和心理体验,将诗歌创作引向象征和隐喻的领域,与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表现有很大不同。但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庞德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他重视的是意象的客体呈现,这种呈现方式与中国古代诗歌“托物寄兴”和“即景抒情”的意象表达方式有某种相似。所以,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一些学者在接受西方诗学观念,强调诗歌的象征性与神秘性的心理体验的同时,开始自觉探讨西方意象派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强调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如孙作云的《论现代派》指出意象派诗歌受到东方诗歌的影响,周其勋的《中国诗坛对于西洋诗之贡献》认为意象派诗“几乎全系含有中国意味”,钱锺书《谈艺录》将《文心雕龙•情采》中的“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与意象派诗人庞德论诗文三类理论相比较,认为它们词意全同。
“意象”作为一个诗学术语,也一直是海外汉学家意象理论研究的重点。余宝琳即是以“意象”为核心研究中国古代诗学,她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一书的导言中指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论的三种方法:一是刘若愚的将文学理论分类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二是魏世德的从某个人的著作出发,讨论其写作背景并追溯其源流的方法,三是像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所采用的方法,即选择“意象”这样的关键词和核心问题去阐释“中国传统如何理解诗的‘意义’的运作”。宇文所安认为,相比前两种方法,余宝琳的研究方法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洞见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意象”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性。
“诗学”,按照学术界有关权威定义,既可以定义为“有关诗歌和文学的一般原理,或者说有关这些原理的理论研究”,其内涵等同于文学理论;也可以定义为作为抒情文体存在的“诗”的理论。无论哪一种定义,如果用于诠释“意象”,与作为哲学美学和艺术本体论的“意象”范畴都是有着明确区分的。诗学意义的“意象”可以理解为关于诗歌艺术形式和一般文艺批评的一个概念,它关注的是诗歌形象构造问题,也可以说是将“意象”看成是诗歌重要的形态和构造诗歌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中国学术界有不少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意象”概念的。比如敏泽说“诗中的意象应该是借助于具体外物,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作者的情思,而非那类物象本身”,胡雪冈说“‘意象’是心意在物象上通过比喻、象征、寄托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袁行霈说“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以上诸人所说的“意象”,无论是指借助某种艺术手段(修辞形式)所产生的情思和心意,还是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主要指的都是关于诗歌形象创造的问题,或者说是将“意象”看成是诗歌重要的形态和构造诗歌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与方法。
诗学意义的意象范畴可以向哲学美学范畴转化,体现哲学美学意识与精神。相比西方美学,中国美学与诗学、诗歌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也更容易形成以“意象”为中心的诗学范畴体系。魏晋至唐被人们看作是意象美学理论的确立时期,它所主要针对的对象也是诗歌。刘勰、王昌龄、刘禹锡、司空图等人正是在总结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审美本体意义的意象理论,强调“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融合统一。中国现代一些美学家对“意象”的阐释也从诗学进入到哲学美学领域。比如,朱光潜用“情景交融”和“形象的直觉”解释诗歌意象和“诗境”的创造,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意象”对于朱光潜美学来说,不仅是一个指代诗学和诗歌美学的范畴,而且具有哲学美学和艺术本体意义。他在《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著作中提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等观点,都是从诗学、文艺学进入哲学美学的领域,将“意象”作为核心范畴以服务于他的美(美感)的基本理论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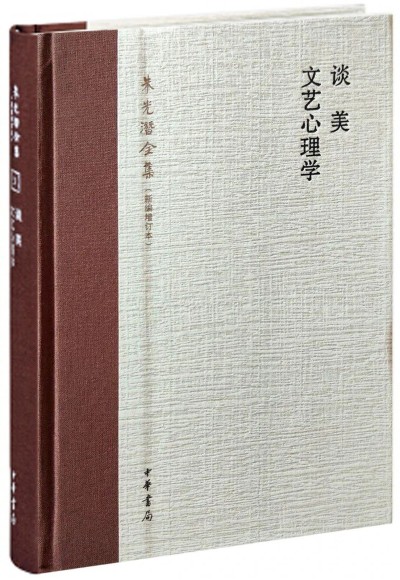
朱光潜著《谈美 文艺心理学》
诗学意义的“意象”也可以停留在一般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意义上,作为结构本文、构造形象的手段和方法而存在。“意象”诗学的研究包含一个重要内容,即诗歌本文和结构类型的探讨。比如,西方新批评理论提出“icon”的概念,认为“意象”(image)不是“意识中的象”,而是“语言中的象”,“是用物质的材料(包括文字)所制成的象”。蒋寅依据此,将“意象”界定为“经作者情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诗意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本文的组成部分”,就是一种关于“意象”的诗歌本文研究。学术界常见的单一意象与整体意象,静态意象与动态意象,比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与描述型意象,构思活动中的意象(作者意中之象)和物化为本文的意象(读者体验到的意象)的区分,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诗歌本文和结构类型的研究。诗歌本文和结构类型的研究,对于诗学意义上“意象”内涵的把握非常重要,但并不一定具有哲学美学本体的意义。蒋寅将“意象视为诗歌本文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反对将“意象”“意境”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所反映的正是诗学(文学理论)与哲学美学本体意义上理解“意象”的差异。从诗学和一般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意义上说,“意象”的确可以看成是一种关于诗歌本文的结构性存在、一种构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但这并非哲学美学本体意义上的“意象”。对于后者来说,脱离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脱离了中国的哲学美学精神,脱离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实践,是很难诠释与理解的。
三、“意象”是一个标示中国哲学美学本体意识的范畴
以上,我们对“意象”范畴进行了哲学美学与心理美学、诗学的语义区分,这种区分的目的是明确“意象”的哲学美学内涵,突出“意象”作为一个标示中国哲学美学本体意识的概念范畴的理论价值。不可否认,“意象”作为一个哲学美学范畴的提出,对于西方美学也具有普遍意义。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idea”的概念,将美诠释为“idea”,有学者探讨过这一概念转译成中文“意象”范畴的内在合理性。不过,依笔者看,这种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后人阐释的基础上的,与柏拉图“idea”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并无直接关系。柏拉图所说的“idea”,如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著名学者陈康所解释的那样,它“出自于动词idein”,“idein的意义是‘看’,由它产生出的名词即指所见的。所见的是形状,因此与morphe同义”,它重视的是事物的“型”,是客观世界的“共相”,而不是主观精神和心理体验的东西。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乃至到18世纪以前的整个西方美学的主导理论,都重视对于这个“型”和“共相”世界的把握,从而建立其支配西方美学两千多年的“摹仿论”。“摹仿论”即是以柏拉图的“idea”(型、相)为基础,重视的是对于事物的原型、原象等实体对象的再现与摹仿,与18世纪以后重视主体心理体验的西方审美意象理论是有着本质差异的。西方对审美意象的重视,应该是从18世纪的康德美学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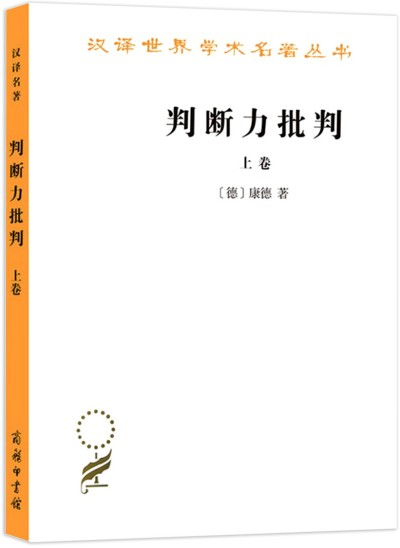
[德]康德著《判断力批判》上卷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观念”(Ästhetische Idee)的概念,他所说的“观念”(Idee)实际上“就是想象力里的那一表象,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它突出了想象和主体心理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象”与“审美意象”十分相似,所以朱光潜和蒋孔阳都将此翻译为“意象”(或“审美意象”)。不仅如此,康德还明确将“意象”看成是标示美和艺术的本体的概念范畴,认为“美(无论是自然美或艺术美),一般地可以称之为审美意象的表现”。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所说的“美”亦近于哲学美学本体意义上的“意象”,它不是知识论的,像柏拉图那样将客观世界的“型”和“共相”放在突出地位,而是突出了心灵、理念的感性显现对于美的意义,所以切近了意象审美的本体。康德、黑格尔之后,不少西方美学家都试图从美和艺术本体来诠释审美意象。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将“审美对象”界定为“通过感受或想象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象”,并认为“凡是不能呈现为表象的东西,对审美态度说来是无用的”,即是将审美对象与审美经验结合起来,将“美”的本体诠释为“意象”。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提出“抒情的直觉”说,他说的“直觉”即情感的表现,直觉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意象,它构成艺术和美的本体。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亦将“意象”作为艺术和美的本体,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这种意象就是通过空间、音乐中的音程或其他一些虚幻的和可塑性的媒介创造出来的生命和情感的客观形式。”从这些表述看,西方现代美学家谈“意象”,主要从艺术创造和美感经验出发,比较重视“意象”的情感性、整体性的特征,其中亦包含对“意象”的直觉和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肯定。
西方现代美学家谈“意象”,还存在着一种常见的阐释途径,就是将其与现象学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强调“意象”的非现实和不在场的特征。比如,萨特提出“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于意象的东西的价值”的观点,海德格尔关于隐蔽与显现、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的理论,杜夫海纳将审美对象称之为“灿烂的感性”的理论,以及将审美的核心看成是“显现”和“气氛”而不是事物表象特征的当代德国美学(以马丁•泽尔和波默为代表),等等,都可以启发人们探讨和认识作为哲学美学本体存在的“意象”范畴的内涵。
相比西方美学,“意象”对于中国美学来说更具有哲学美学本体的意味。中国文化是尚象重象的文化,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就包含着丰富的“象”的文化基因,这从远古神话和器具意识的起源、从甲骨文开始的汉字构造、《易经》的卦象符号就充分体现出来了。“象”也如宗白华说,“即中国形而上之道也。象具有丰富之内涵意义(立象以尽意),于是所制之器,亦能尽意,意义丰富,价值多方。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实用的溶于一象”,它成为中国重视意象审美的哲学美学思维的重要起点。先秦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在对“象”思维和文化精神的哲学美学阐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与观点。如老子将“道”“气”“象”联系起来的哲学观念以及“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命题的提出,庄子的“象罔”哲学观念和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解,《易传》“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命题的提出,先秦儒家以“象”比德和《诗》之“比兴”的观念等,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哲学基础。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便可以说是以“意象”为中心展开的,对“意象”的哲学美学思维和理论创构贯穿了中国美学史的整个过程,这从刘勰、司空图、王昌龄、张怀瓘、孔颖达、苏轼、朱熹、严羽、王廷相、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人的美学诗学理论建构中不难看出。这是不同于西方美学的。西方主要是在18世纪以后才将“意象”作为哲学美学关注的对象。正是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美学家将“意象”作为重要的哲学美学范畴提出来并进行美和艺术本体论的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叶朗就提出“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观点。这一看法在学术界虽存在着争议,但将“意象”看成是中国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认为意象审美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精神和思维特点,则几乎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意象”对于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审美的价值,也在朱光潜、宗白华、叶朗、汪裕雄、张世英、叶秀山、杨春时、张祥龙、王树人、陈望衡、朱良志、朱志荣、彭锋等中国学者的美学理论和研究中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重要性,也被一些海外汉学家和西方学者充分意识到。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就认为,叶朗所提出的不应该从美而是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中国美学和文学的观点非常重要。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亦将审美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线索,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无法之法”“天人合一”“自然创造”等问题出发,凸显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意象”一词,无论对于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美学来说,都具有“意中之象”或者说“表意”的意谓与内涵。但是,西方美学和文论中的“意象”,特别是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美学对“意象”的阐释,根源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念,根源于知、情、意的心理意识区分;审美意象的创造属于“情”的领域,是一种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审美观念,其心理美学的意味突出。而中国古代对于“意象”的理解则主要是哲学而非心理美学意义的。“意象”范畴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美学背景下,是中国古代诗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是人与天地万物交融一体的哲学美学精神的体现。意象审美所追求的不是“象”所直接呈现出来的意义,而是隐含在“象”背后更深层次、具有言外之意和丰富的人生意蕴、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体验的东西。“意象”审美对于中国美学最大的意义,如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所说,“是精神的美和艺术”,“是想象力突破了概念的僵化的思考和固定化,是想象力带来了动的想念的更为自由的漫游”,它超越西方对象化、实体化思维,重视主体精神和心灵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恽寿平《题洁庵图》)“意象”审美的要义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要超越现实、走向精神的审美追求。关于这一点,中国现代美学家有着明确的认识。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将艺术意境(意象)阐释为“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朱光潜将“意象”看成是情景相生的产物,强调意象(诗的境界)是由心灵创造而来,时时刻刻都在创化中,永远都不会复演,等等,都很重视中国美学中的“意象”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关系。叶朗则说得更为明确,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提出“美在意象”理论,就是要继承中国意象美学理论的传统,“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
中国古代对于“审美意象”的理解,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以“意”为主导,将审美意象看成是审美主体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又充分意识到,意象的生成与创造,又必须以“象”为载体,做到意与象的交融。审美意象即是象与意、物与我、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与自然融合。审美意象可以说是揭示了人与世界、人与万物最本源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经验在自己所生活的本真世界中的呈现。“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手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温庭筠《过分水岭》)溪水的有情与无情与人的心灵、人的生活是同处共在的,它是在一个懂得生活、有着丰富的诗意感受的人眼前呈现的,而对于一个失去了生活感觉和感受的人来说,则是无意义的。这正像萨特所说的,一种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风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存在,本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本就与人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而审美意象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的风景美显现出来。用马丁•泽尔的话说,“对于审美直观,重要的并不是某物的实际,而是其显现的方式”,即美不是一种特别的事物,而是事物处于显现状态。审美意象的创构或者说审美意象本体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事物的美得以显现。中国古人将“意象”本体阐释为“情景交融”(情景合一),这里所说的“情景交融”如王夫之所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惟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这是存在论意义上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并非有了主体与客体的心理区分,将“情”与“景”区分开来,然后才通过主体心理的努力而达到统一,而是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实不可离”的“情景合一”的世界中,情与景、心与物、人与世界原本就是不可分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真意、有诗意的世界,但这种真意、诗意在日常功利的世界中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审美意象本体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将这种隐藏着的真意、诗意重新显现出来、绽露出来。用叶朗的话说,就是:“意象世界是人的创造,而正是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了生活世界的本来面貌。”

叶朗著《美学原理》
意象作为标示中国哲学美学本体意识的范畴,具有圆融性、生成性、超越性和情感体验性的特征。“圆融性”是说审美意象是一个心与物、意与象、形与神、情与景圆融自洽的有机整体。中国古人讲“意与境会”(权德舆),“思与境偕”(司空图),“意象浑融”(胡应麟),“情景相融而成诗”(谢榛),“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王夫之),等等,强调的就是“意象”圆融性的特点。“圆融性”强调的是审美意象的独立自足性,强调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同于物理性、日常功利性的世界的。中国古人说,“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恽南田),等等,即是将意象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同于物理性的、日常功利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情与景等诸种因素是紧密交融在一起的,它不再是人与对象世界的限隔,也不再让对象世界为人的精神世界所奴役,而是人与万物、人与世界的相亲与相通,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交融。在这样的世界中,万物向人的心灵敞亮,万物与人的情感交融,人则在这万物明朗、敞亮、情与景交融的世界中获得充分的精神享受与满足。
“生成性”是说审美意象的创造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审美意象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不断生成、创造的,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成果。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美的人生态度表现为两点:一是把玩现在,二是美的价值寄于过程的本身,无论是“把玩现在”还是“寄于过程”,都是一种意象美的生成,都是个体审美直觉感兴的产物。王夫之谈诗,一再强调“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也是强调个体直觉感兴对于审美意象生成的意义。不过,这种个体直觉感兴并没有割断其与历史、文化的联系。王夫之说:“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谓之曰过去。不知其未尝去也。有将来者焉,流之归也。而谓之曰未来,不知其必来也。其当前而谓之现在者,为之名曰刹那,谓如断一丝之顷。不知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非仅刹那也。”这里所说的“刹那”和“念中”即是直觉感兴,但它并没有中断历史,而是将历史(过去—现在—将来)包含在“刹那”的一念之中,美的意象正生成于这一念之中。它是瞬间直觉的产物,却依然可以照见历史,呈现一个完整的、有生命力的世界。中国古代美学将“情景交融”作为审美意象的基本规定,也具有这样的意味。叶朗说:“我们每个人本来就生活在‘情景合一’的世界之中。这个‘情景合一’世界,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世界,而不是史前的生物世界。”意象世界是一个情景交融的世界,是个体审美活动直觉感兴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没有个体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融合,没有个体向社会历史文化的生成,这种个体审美的直觉感兴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超越性”是说审美意象的创造具有超越现实的品格,它不拘泥其感性对象的形式,而是超越感性形态而走向精神价值的层面,以有限的形式去表现无限丰富的内容。将“超越性”作为审美意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哲学是以“象”体“道”的哲学,中国古代美学之所以将“意象”作为美和艺术的本体看待,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一种感性形象的存在,更重要的在于它可以超越“象”的感性存在而进入“道”的精神层面,以象显意、以象体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与解放感。将意象看成是具有超越意义的现象,或者说将超越作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也意味着对传统的认识论、反映论的理论模式的超越,意味着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超越。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与西方现象学美学思想形成了对应。西方现象学美学用意向性来解释美,反对将美看成实体的属性,就包含从非现实、超越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美的本体和现象的思想。不过,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审美意象超越性的理解,主要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生命价值的体现,是一种高远的生活境界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宗白华说:“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审美意象创造的就是这样一个“灵”的生命空间,以感性形态的物象为依托,同时又超越这种感性的物象形态,于清明澄澈中使人的生命超越现实生活喧嚣,见出一种心灵的自由。张世英认为,“要做一个‘真人’——一个有精神的人,我们就既要面对现实,有欲有求,又要超越现实,看到现实以外的高处远处”,所以“中国的意象之美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提高精神境界的一个最好、最大的启示”。也可以说,意象审美使人们超越感性的、物欲的需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情感体验性”也是审美意象重要的特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国哲学和美学是以情感会通世界的,将万物看成是一个有情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如王夫之所云:“言情则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在这个世界中,天与人相通,情与景相互生成,万物如其本然地存在,日生日新,于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无穷变化,呈现出生命最真实的状态,带给人新鲜无尽的体验与感受。将情感体验作为审美意象的基本特征,并不排斥审美意象包含着知觉、认识、理性、思维的因素。但必须明确的是,审美意象创构中的知觉、认识、理性、思维等因素,在本质上不是属于认知和认识论范畴的,而是与情感紧密交融在一起的。“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寒山《寒山吾心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同是天上的一轮月亮,或伤感,或澄明宁静,或清幽孤逸,或凄清冷寂,或欣喜希冀,或苍凉雄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彩与意蕴,就在于诗人所表现的月亮世界,带上了浓浓的情意,充满了爱,充满了人生的情趣。张世英在谈到审美直觉性时提出“思致”的概念。他说:“‘思致’是思想—认识在人心中沉积日久已经转化(超越)为感情和直接性的东西。审美意识中的思就是这样的思,而非概念思维之思的本身。”张世英所说的“思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审美意象创造活动中的理性与思维因素,它说明审美意象并不排斥理性、思维的因素,而是与人们的情感态度和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而非逻辑认知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结语
以上我们对“意象”范畴的语义内涵进行了辨析,这种辨析是从哲学美学本体意义上展开的。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意象”范畴与心理学、诗学意义上的“意象”范畴有一定联系,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它的意义不在于将“意象”作为一个心理学对象予以美感经验和心理事实的还原,也不在于将其作为文学和诗学的对象从诗歌形象创造和本文批评意义上去诠释理解,而是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精神与理想,特别是以“象”显“意”、以“象”体“道”、情与景、心与物一体交融的美学精神与理想。这种精神与理想,不仅仅具有历史传承的意义,而且可以与现代美学结合起来予以发扬光大。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关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的、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象)想到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意),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让你的生活充满情趣、充满诗意。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审美意象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67)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毛宣国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1期(总第110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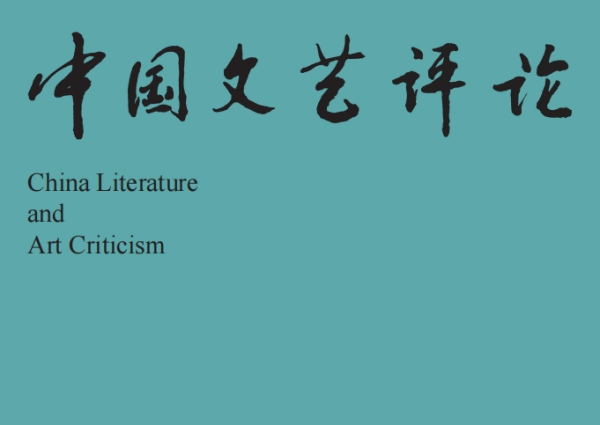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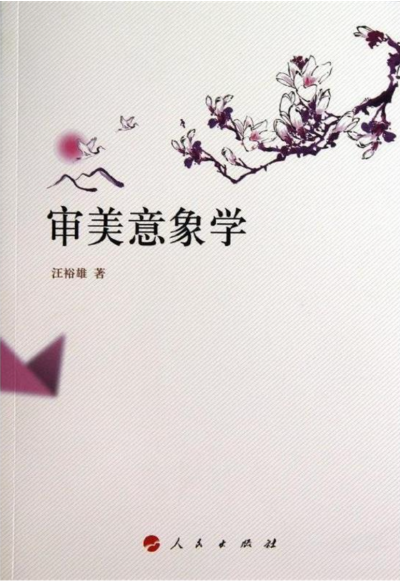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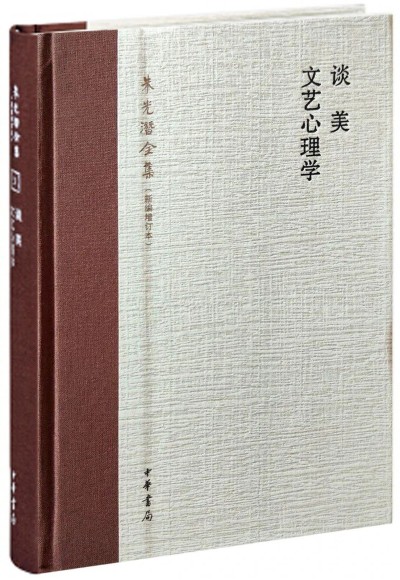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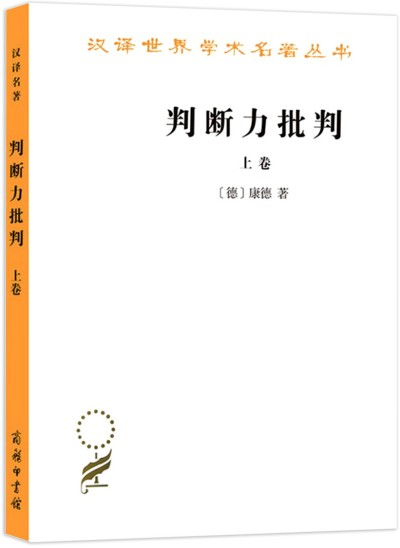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